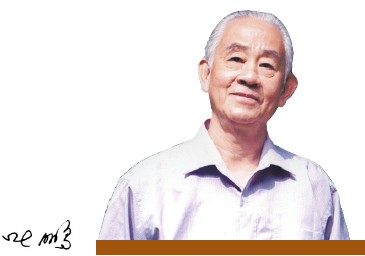-
沒有記錄!
吳佩孚與西工兵營
2013/9/6 10:16:02 點擊數(shù): 【字體:大 中 小】
吳佩孚(1874~1939),字子玉,時稱“蓬萊秀才”、“洛陽王”,山東蓬萊人,北洋軍閥直系首領(lǐng),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長期經(jīng)營洛陽,遙控北京,左右政局,是登上美國《時代》雜志封面的第一個中國人。
他自詡為“四不將軍”:不做督軍,不住租界,不蓄私產(chǎn),不娶姨太太;實乃軍界屠夫:鎮(zhèn)壓“二七”大罷工,殺害“工運”領(lǐng)導(dǎo)人林祥謙等;其個性鮮明:蔑視日寇,至死不當(dāng)漢奸,終被日本軍醫(yī)趁拔牙之機(jī)割斷喉管而殞命。
一個書生,一介武夫,一代梟雄;
大起大落,大毀大譽,大奸大忠。
在解放路與凱旋路口找到了吳佩孚閱兵臺
沿著凱旋西路向東走到解放路口,向右側(cè)一看,就能看到吳佩孚閱兵臺。
閱兵臺門臉向南,屁股朝北。站在凱旋路與解放路交叉口,明明能看見這座建筑,可就是看不到它的正面(圖①),要想觀其全貌,必須從中國空空導(dǎo)彈研究院的西院進(jìn)去,才能繞到它跟前。其時正是午后兩點,驕陽似火,采訪車被攔在這家單位大門口。
忙不迭地辦完了出入手續(xù),這才得以和閱兵臺打了個照面。仔細(xì)看,閱兵臺用水泥筑成,寬敞、高大,莊嚴(yán)(圖②)。前臺,是4根紅色大立柱,柱子之間空無一物,視野開闊,便于將軍閱兵;臺上空間很大,呈長方形,可容納二三十位將軍列坐;后臺是三間貴賓室,供長官休息和接見將士時用。
站在閱兵臺前,心中涌起復(fù)雜的感覺。
想當(dāng)年,當(dāng)時中國裝備最先進(jìn)的新軍從這里列隊走過,那是北洋軍陸軍王牌第三師的驕傲的官兵們。槍刺和馬刀挑起的寒光在閃爍,陸軍步兵和騎兵踏起的煙塵,彌漫在東下池北邊的這塊土地上,還牽動著中國其他軍閥的目光。當(dāng)時的吳佩孚,被稱為半個帝王;當(dāng)時的洛陽城,實際上是中國的首都。
由于吳佩孚雄踞洛陽,所以洛陽早已成為中國政界和世界列強(qiáng)關(guān)注的焦點,閱兵臺上站著中國元帥,也站著美、英、日等國的軍事觀察團(tuán)成員。那場面,那氣勢,那軍歌,那口號,都是當(dāng)時中國最前沿的風(fēng)景。
可是,歷史仿佛在不經(jīng)意間喊了一聲“稍息”,這個閱兵臺便懶洋洋地不再動彈了,而光陰仍往前走了87個春秋。87年后的今天,這里梧桐列隊,綠草如茵。閱兵臺被打掃得干干凈凈,環(huán)顧左右,再無他物;傾聽周遭,寂靜無聲,忽然心中便有了一些感觸:那歲月的掃帚,已把吳佩孚這樣的大軍閥掃地出門,只留下一些文字,在那里輕輕訴說。
任你叱咤風(fēng)云,終是匆匆過客!那么,吳佩孚這個過客,在此處留下了什么遺蹤呢?
當(dāng)年的吳佩孚叱咤風(fēng)云 一度被譽為“常勝將軍”
吳佩孚在當(dāng)時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吳佩孚1874年出生于山東蓬萊。其父吳可成開了一家雜貨店,家境一般,其家世沒啥可講的,但若論起蓬萊這個地方,卻是沾了點神仙氣。“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古代帝王們都愛到此處尋找長生不老藥。蓬萊閣下,原有一座水城,是抗倭名將戚繼光水師的訓(xùn)練基地。雜貨店老板吳可成很有點愛國心,所以,當(dāng)那個未來的大軍閥呱呱墜地時,他給取名吳佩孚。啥意思呢?說是抗倭名將戚繼光字佩玉,所以這孩子名“佩孚”,字“子玉”,他巴望這小子長大成人后,抵御外侮,成為英雄。
距蓬萊不遠(yuǎn),有一座田橫島。西漢初年,田橫的五百名部下在這里送別了田橫,讓他去洛陽朝拜劉邦。可是,很快傳來消息:田橫走到偃師,不愿見劉邦,自刎了。于是五百壯士也紛紛自刎,追隨田橫而去,一時間血濺長空,釀成千古俠云。
吳佩孚由傳統(tǒng)文化養(yǎng)分泡大,不但秉承了俠義之氣,還織就了洛陽情結(jié)。他愛讀書,看到夏、商、東周、東漢、魏晉各朝都以洛陽為都,而歷代英雄豪杰,無論身在何地,最終還是要紛馳洛陽;加上少年吳佩孚喜歡《易經(jīng)》,知道洛陽是《易經(jīng)》的故鄉(xiāng),所以更加向往洛陽,發(fā)誓一定要到洛陽成就一番事業(yè)。
吳佩孚14歲時死了爹,22歲時考上秀才,23歲時得罪了本地豪強(qiáng),只好到北京流浪。他住在客棧里,靠賣字和算卦勉強(qiáng)糊口,饑一頓飽一頓,有稀沒稠的。一天,境況窘迫的他被堂兄吳亮孚撞見,堂兄見他如此落魄,便勸他棄筆從戎,前去投軍。
也算是他會投軍,一投兩投,便投到了曹錕手下;三爬兩爬,就爬到了團(tuán)長的位子上,再由團(tuán)長升為副師長。民國六年(公元1917年),曹錕受命攻湘,以吳為前敵指揮,率軍南下。吳深信“兵貴神速”,更以“不怕死”著稱,頭裹青布,匹馬前導(dǎo),為士卒先。此役,他下岳州、取長沙、占衡陽,勢如破竹,一戰(zhàn)成名。接下來,他又連打勝仗,被譽為常勝將軍。至1919年底,吳佩孚已成為地位僅次于曹錕的直系軍閥首領(lǐng),并于次年聯(lián)合奉系軍閥張作霖,大敗皖系勢力,從此直奉聯(lián)手,共同控制北京政府。
吳佩孚深謀遠(yuǎn)慮:一山難容二虎。皖系消亡后,直系與奉系的合作豈能長久?直奉兩家終有一場生死較量。曹錕也看到了這一點。兩人密謀:必須盡快訓(xùn)練一支裝備最先進(jìn)、戰(zhàn)斗力最強(qiáng)的新軍作為殺手锏,打敗張作霖!曹錕說:把訓(xùn)練基地放在京津地區(qū)吧?吳佩孚說:不行,得放到洛陽。
熟讀史書的吳佩孚,深知洛陽地理位置優(yōu)越、文化底蘊深厚,所以決定屯兵洛陽。他對曹錕說:“洛陽為十省通衢,四通八達(dá),地理居中,夫所謂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如果我以重兵駐洛陽,則居中可以御外,宜于武力統(tǒng)一天下。”1920年9月2日,吳佩孚率領(lǐng)他的陸軍第三師進(jìn)駐洛陽。當(dāng)天,北平政府任命吳佩孚為直魯豫巡閱副使。
他不敢破壞帝都?xì)饷} 撇開老城擴(kuò)建“西工兵營”
吳佩孚來到洛陽。當(dāng)時的洛陽城破爛不堪,全城人口不過二三十萬人。吳佩孚卻對洛陽心存敬畏,他走遍四關(guān)四隅,祭了祭關(guān)林廟里的關(guān)公,拜了拜文廟里的孔子,那雙踏平無數(shù)敵陣的軍靴,從洛陽的青石大街上走過時,一點兒也不敢放肆。
長期研究《易經(jīng)》并篤信風(fēng)水學(xué)說的吳佩孚,不敢在老城基址上建兵營,擔(dān)心破壞帝都?xì)饷}。他找來風(fēng)水先生,仔細(xì)選擇兵營營址。最后,風(fēng)水先生建議他在西關(guān)以西、七里河以東、東下池以北、金谷園以南建兵營。
其實,他這不能算是建設(shè)兵營,只能說是擴(kuò)建兵營。因為在他來洛陽之前,袁世凱已經(jīng)捷足先登了。那是民國三年(公元1914年),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在素稱軍事重鎮(zhèn)的洛陽修建新式兵營,在此訓(xùn)練新軍,作為他登基稱帝的軍事資本。兵營建了兩年時間,于民國五年(公元1916年)竣工,占地200萬平方米,建有房屋5000余間,耗費白銀170萬兩。由于該工程位于當(dāng)時洛陽城的西關(guān)外,老城人多來此打工,所以稱這里為“西工地”,后簡稱“西工”,由此派生出“西工兵營”和今天的“西工區(qū)”兩個稱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