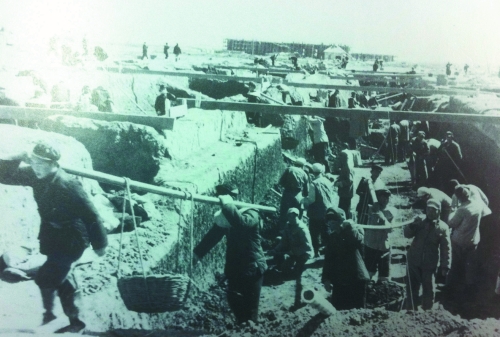-
沒有記錄!
關注:洛陽何家天井窯院的故事
2013/5/8 17:46:08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天井窯院全貌

天井窯院內的“上房”室內

雕花的門墩兒

天井窯院內的老井
核心提示
近日,位于瀍河回族區樂善街的何家天井窯院重現昔日繁華景象,不少市民前去探訪(詳見本網報道)。是誰,何時建造了這座代價高昂、裝飾考究的古宅?它經歷了哪些風霜?記者多方走訪,挖掘埋藏在這座百年窯院中的故事。
1 窯頭嫁千金,15萬塊青磚筑“豪宅”
這座長寬各8米、深7.5米,有5間窯洞的天井窯院,從里到外全部用青磚包砌。屋門統一雕刻銅錢連串鏤空花形,門口均有兩個菊花樣紋路的雕花門墩兒。在院墻四周高約4米和6米處,各有一道青磚砌成的花邊,院頂有高約半米的鏤空花墻。
大氣的院落和考究的做工,顯示著這座老宅曾經的風光。據戶主何景儒介紹,這座窯院是清末他的爺爺何來定迎娶奶奶趙氏時所建造的。建造這樣一座“豪宅”,要歸功于他奶奶的父親——當時在洛陽名噪一時的趙窯頭。
趙窯頭真名叫啥,如今已無從考究。當時,瀍河回族區一帶北邙上皆為燒制青磚的窯場,而趙窯頭協調管理著所有窯場,在當地“絕對是個人物”。
名聲顯赫的趙窯頭膝下只有一女,到了出嫁年齡,趙家千金相中了何家小伙。趙窯頭愛女心切,加之坐擁數個窯場,便出資建造了這座青磚包砌的“豪宅”。“聽老人們說,15個人建這個院子,整整干了半年,僅圏窯和砌墻的青磚就達15萬塊。”何景儒說。
星移斗轉,邙嶺一帶的土窯廢的廢、塌的塌,唯有何家的天井窯院依然堅固如初。若不是院墻表面的青磚已風化剝落,陌生人很難相信它已有百年歷史。
2 層層地磚下,暗藏“密室”
如今,何景儒一家已搬出窯院四五年了。幾年前,何景儒的幾個兄長曾提出填埋窯院,遭到了他的反對,這里有太多他無法割舍的回憶以及未知的秘密。
一年大雨,何景儒發現東側一孔窯洞不斷往外涌水。他十分不解,問父親:“人家是從院子里往屋里流水,咱家咋是從屋里往外流呢?”
老父親不作聲,待雨停后,走進涌水的窯洞,從門口沿左側墻根丈量幾步,跺跺腳說:“挖吧!”
何景儒更疑惑了:父親所站之處,與其他青磚地面并無二樣。他找來鐵锨,沿著磚縫一一撬起,青磚撬開幾層后有一塊厚木板,掀開木板,一個長寬約七八十厘米的正方形地洞出現在眼前。
“我在這院子里長了幾十年,竟不知道還有這地洞。”何景儒回憶說。他跳下地洞,經過一段幾米長、可容一成年人直立行走的過道后,一個寬闊的密室讓他目瞪口呆。
這是一個面積至少30平方米的密室,其一端與自家窯洞相連,另一端也有長長的過道,直通窯院側上方鄰居家院子中一口水井半腰的井壁。父親告訴他,這是建造窯院時就開鑿的密室,用來儲藏財物、糧食,兵荒馬亂的年代,還可作逃生之用。由于何景儒生在太平世道,密室無用武之地,父親也就沒告訴他。
得知地下的秘密后,鄰居擔心密室常年浸水坍塌,自家院子也會下陷,遂運土從井口填埋了這個密室。
同樣的“機關”,何景儒在自家窯院西北角的水井中也發現一個。站在水井旁,順著何景儒的手指方向,只見在距離地面約七八米處的井壁上,有個直徑不足1米、黑洞洞的洞口。何景儒說,他曾下去看過,這個洞并無其他出口,大概只是用來存放財物所用。
3 專家呼吁:
應盡快保護“顯性歷史”
現在,何景儒閑暇時候,常到院子中修葺整理。沿著狹長的樓梯走進院子,這里恍若一個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院子四周,葡萄、櫻桃幼苗才吐新芽,墻根處3個大水缸中,紅艷的金魚分外耀眼;抬頭仰望,鄰家的石榴樹旁逸斜出,枝頭上還掛著幾個隔年未摘的干石榴;不知是誰家的笛聲,斷斷續續縈繞在窯院上空,營造出一個隱于鬧市中的安逸之所……
古建筑研究學者、洛陽市規劃建筑設計研究院原總建筑師王鐸稱,天井窯院作為洛陽周邊一種獨特的民居建筑,可以直觀判斷出古代洛陽的氣候、土質及人文風貌等,有極高的文史研究價值,可以說是洛陽的“顯性歷史”。
早在20世紀70年代,日本建筑學者就將其命名為“生土建筑”,列入建筑形式的一種。王鐸也曾對此展開過調查研究。如今,隨著天井窯院逐漸淡出歷史舞臺,像何家天井窯院這樣的建筑,應及早重視、保護、修復,為后人留下一份建筑、文史研究的資料。
目前市民可免費參觀。地址在瀍河回族區民族路與樂善街交叉路口往北五六百米。(記者 王妍/文 見習記者 杜卿/圖)(原標題:關注:洛陽何家天井窯院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