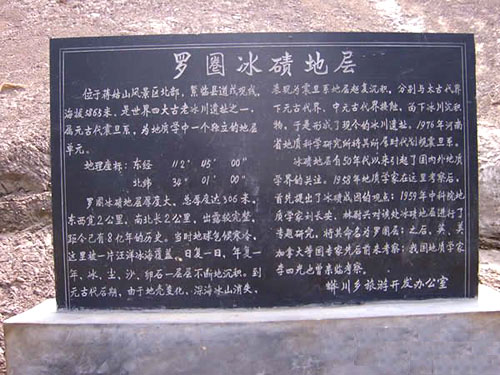-
沒有記錄!
水經注:流淚的芝河
2013/11/11 9:03:18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芝河是北汝河右岸的一條支流,匯聚擂鼓臺、落鳧山、平頂山、馬棚山之水,四季不絕。
芝河的源頭在落鳧山北麓,兩道山谷夾一丘土嶺,若二龍戲珠。嶺頭有兩間廟舍,下百多級石階,東西相對也是一處寺廟,據光緒年間碑文記載,是李姓大戶的家廟——“十二老母廟”。兩
道山谷在寺廟前匯合,雨多時水聲響些,旱天就只剩山泉隱隱滴落了。
寺院周圍樹稠林密,西面土崖上有十盤葛藤,根似龍爪,枝蔓凌風,抓住苦楝和構樹,攀爬百多米,懸成一軸明清長卷。下去不遠,巖基裸露,溝谷跌落,形成四個水潭。
陡峭的紫色山巖,被水沖洗得潔凈光滑。灌木和雜草從巖縫間垂下,斜生橫舉的大樹幾乎遮蔽了上面的天空。大小都不過十幾平方米,潭水黑釅釅地沉一層落葉,蝌蚪一樣的小魚兒,在透過樹陰落在水中的云影間游動。
人跡罕至,鳥有點吵,好聽是水的聲音,細細地磨過巖石,蹦跳著落入潭中。人在那里站久了,心,不知不覺就成了潭水。
過了第四個潭,由于山泉加入,線流成溪。一路繞過村莊、山崖、小樹林和莊稼地,在大大小小的礫石間明滅幾公里,流入水庫中。
鏵角山和鳳凰山相向聳立,那個地方叫土門,水庫就叫土門水庫。建成于1959年5月,存蓄平頂山北麓9個山頭的洪水。1963年冬灌區配套:壘砌干渠5700米,支渠9250米,車橋、路橋12座。澆灌5000畝土地。庫水環繞的村莊叫竹園,綠竹白鵝、青堂瓦舍,秋來黃葉瑩然、紅葉洇人。
可惜幾年前這里成了一家電廠的灰坑。
水被焚燒后的煤灰憋往,好容易從溢洪口滲出一點兒,稠乎乎沒有了水的模樣。經過幾個沉淀池,才流得稍稍暢快些,根本稱不上河,只是一條邁邁腿就能過去的小水溝兒。
過雙橋到張店村,有一處2002年修建的水閘,是“替代工程”。新水閘上去不遠,是一座1970年10月建成的單孔石橋。北半面過車,南半面疊架五孔渡槽。因為無水可灌,西去雙橋的石渠大半毀了,繞村子東走的,成了護村的“寨墻”。聽村民說,芝河曾經有一人多深,能洗澡,能澆地,現在連河床都快淤平了……
一匹棗紅馬在橋下吃草,雉雞在不遠處的楊樹林里高一聲低一聲地鳴叫。芝河隱身在灌木雜草間,成了一道灰禿禿的泥印兒。山彎里有幾片樹林,仿佛還在懷想芝河迸濺涌流的好景致。樹枝上有一只黃口嫩腿的小鳥兒,小小的胸脯犁著遠來的風。我讀不懂它的眼神,但它讓我想到了剛剛在網絡上下載的圖片——寧靜的瑞士村莊。
紛亂的思緒中,我聽見水聲迸濺,不是源頭親切的低語,是大自然悄然滴落的清冷的淚水。
人畢竟是有適應能力的動物,就在張店和李口之間,幾十米寬的芝河灘凸凹成一百多畝的莊稼地,凸起的是黃豆,凹下的是水稻,被稱作“芝河”的小溪蜿蜒其間,幾不可見。
李口村一村三壩,上面是幾百畝波推浪涌的蒲草。中間那處水面空闊,卻不能飲牛喂羊。最下面的干脆被肥膩的水生植物遮蔽,看不到一星水光。
再往下十幾里,七八戶農家正在用水泵抽水澆地。
如果你聽得見芝河的哭泣,那她絕不是在為自己唱挽歌。(曲令敏溫書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