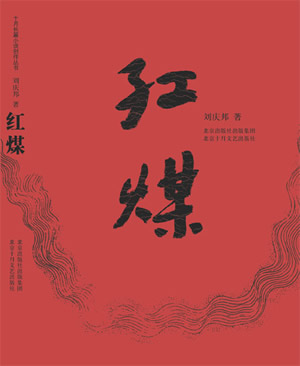-
沒有記錄!
生生死死小煤窯 劉慶邦最新長篇《紅煤》問世
2013/7/24 17:17:49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2005年,劉慶邦的《臥底》《看秋》等一系列以小煤窯生活為題材的中短篇小說頗為引人注目。2006年伊始,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他的以小煤窯為題材的長篇小說《紅煤》,繼續把筆頭對準生死煤窯里的那些礦工們的生活。不過,這次,他把重點放在了人性的變異上。
劉慶邦被稱為當代“短篇小說之王”,中國煤礦文學的旗手。《紅煤》更是標志著他在長篇創作藝術上取得了的長足的進展,是一部反映當代煤礦生活現實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故事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農民出身的宋長玉,是一個與國營喬集煤礦簽了5年合同的輪換工。如果他能在5年中表現突出,就有5%的希望轉為正式工,從此躋身于他朝思暮想的城里人之列。
他為了能夠轉成正式工,先是處心積慮地追求礦長的女兒,就在美夢將要成真之際,不想被礦長看穿,被礦長借故開除了,這件事他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種子。痛定思痛后,他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追求,這回他瞄準的是一位村支書的女兒。最終,他如愿以償,登上了展開自己宏圖的舞臺。他開了小煤礦,當了礦主,買通了鄉干部,讓自己的親戚當了村支書。
隨著金錢滾滾而來,地位步步高升,他的各種欲望急劇膨脹,原先的自卑化作了一種惡意的報復,將人性的惡充分釋放了出來。他先后三次舉報,告原先開除他的唐礦長的狀,最終將唐礦長送進了監獄。隨著煤礦的無節制開采,昔日泉水叮咚、荷花遍地的紅煤廠的水源斷了,連吃水都發生了困難,人們的生存環境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宋長玉的煤礦也發生了透水事故,死亡礦工17人。在事故面前,他逃之夭夭。
宋長玉從農民到礦工、到小煤礦礦長又到礦難逃逸者的經歷令人扼腕,發人深思。一方面,宋長玉力圖改變惡劣的生存境遇,但他卻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最后變成了一個扭曲的靈魂。另一方面,在宋長玉身上還體現出農民對城市的向往和城市對農民的不接納。可以說,正是這種矛盾促使宋長玉走進煤礦,進而一步步走上一條不歸路。
小說以精微細膩的描繪見長,詳盡地展示了主人公宋長玉攀附、奮斗、復仇、墮落的過程。其精到之筆讓人嘆服。寫到滿身都是煤塵的井下工人洗澡時,書中這樣描述到:“泡澡也有個火候問題,手上和腳上的紋路最多,最深,縫隙也最多。手腳在熱水里泡久了,油性很大的煤塵有可能會浸到肉皮里去,再想洗干凈就難了。”沒有在煤礦深入生活過和細致入微的觀察力,是很難寫出這樣貼近生活的文字的。
另外,作者有著在農村生活19年、煤礦工作10多年、當煤炭報記者近20年的經歷,對煤礦生活特別熟悉,在寫作前又一再深入小煤窯體驗生活。他對人物的心理描寫,精微細膩,行文中有一種舉重若輕的氣度,在氣定神閑中游走,雖然對井下生活著墨不多,但如數家珍,令人贊嘆。例如小說開頭部分礦工洗澡一節,將宋長玉洗澡的過程用了6000多字來精細地描繪,使我們能夠觸摸、體悟到煤礦生活的真髓。
已寫過多部反映煤礦題材的小說,此次為什么又把眼光瞄準煤礦呢?劉慶邦說:“我認為煤礦的現實,就是中國現實的縮影,而且是更深刻的現實。在中國向工業化、城市化進軍的過程中,煤礦既不是農村也不是城市,但它又是農村又是城市。煤炭占中國全部能源構成的70%,換句話說,中國的能源大廈,是靠千百萬礦工的肩膀支撐的。他們的生活是與中國社會的現實緊密相連的。”
作為一名作家,劉慶邦寫作的著眼點從不在風花雪月,不在繁華都市,而是一直關注著社會底層的人們,關注著農民、礦工。他說自己就是從底層出來的,在農村當農民是一種底層生活,在礦上當礦工也是一種底層生活,到了報社后這么多年他還與煤礦保持著很緊密的聯系。
有人說他的作品太過沉重,而劉慶邦認為生活本身就是沉重的。但不管寫多么沉重的東西,劉慶邦總是抱著善良、善意的態度,賦予作品一些理想的東西,力圖通過自己的作品給人帶來希望。他毫不諱言地說文學就應該是勸人向善的,是改變人心的。他說:“人生總是在一個困境當中,作家有責任來認識這個困境、反映這個困境,目的是使人心不斷得到改善,我認為這是文學的本質,也是作家的社會責任。”
劉慶邦對礦工們總是懷著深深的敬意。他說:“中國礦工是一個有著特別犧牲精神的特殊群體。他們在地層底下生活,付出的勞動特別大,對社會的貢獻也特別大,但得到的回報卻很小。中國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付出了很大代價,礦工是首當其沖的,他們是最值得寫的群體。”
對《紅煤》主人公宋長玉,他是抱著理解的態度來展現這個人物的。他說,宋長玉并沒有生活中的原型,但相似的礦工他是熟悉的,素材都是他長年生活積累的。有的是以往礦山生活的回憶,有的是近年在煤礦體驗生活時新得到的感受、體會,再加上自己的想像力。他把自己的經歷及心路歷程都融化到作品中去,用心理邏輯去推動人物發展,他說這樣才能“把人物寫得貼心貼肺,有血有肉”。他認為作家“必須富有想像力,賦予作品心靈化的東西”。人的想像從哪里來?劉慶邦強調,想像要有一個基礎,這個基礎就是作家的生活、經驗。
“如果寫作沒有人生經驗作支撐,就很難寫出比較厚重的東西。”即使現在是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劉慶邦每年仍要抽出不少時間去煤礦體驗生活。每次到礦上,他和礦工們都“相處得像兄弟一樣”。他說:“作家深入生活,不僅是為了收集素材,更重要的是情感上的積累。作家只有保持對生活的激情,才能進入創作狀態。”
當問起劉慶邦為什么把書名叫做《紅煤》時,他回答說,一方面確實有一種煤和鐵礦伴生、里面有紅筋、發熱量大又耐燒的被稱為“紅煤”的煤。另一方面,去年一年我國礦難就死了幾千名礦工,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燒的煤里,是有礦工的血、淚、汗水在里面的。但是如果以為《紅煤》是寫礦難的書,那就錯了。事實上,在這本書里,劉慶邦是在穿越礦難寫人情,寫人性。與其說《紅煤》是一部煤礦小說,不如說它是一部在深處的小說更恰當。這個深處不僅在挖煤的地層深處,更在人的心靈深處。劉慶邦用掘進巷道的辦法,在向人情、人性和人的心靈深處掘進。也正如此,他的這部作品才具有了打動人心深處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作者簡介
劉慶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農村。當過農民、礦工和記者。現為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一級作家,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
著有長篇小說《斷層》《遠方詩意》《平原上的歌謠》等五部,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集《走窯漢》《梅妞放羊》《遍地白花》《響器》等二十余種。
短篇小說《鞋》獲1997至2000年度第二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神木》獲第二屆老舍文學獎。根據其小說《神木》改編的電影《盲井》獲第53屆柏林電影藝術節銀熊獎。曾獲北京市首屆德藝雙馨獎。
多篇作品被譯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等外國文字。【原標題:生生死死小煤窯 劉慶邦最新長篇《紅煤》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