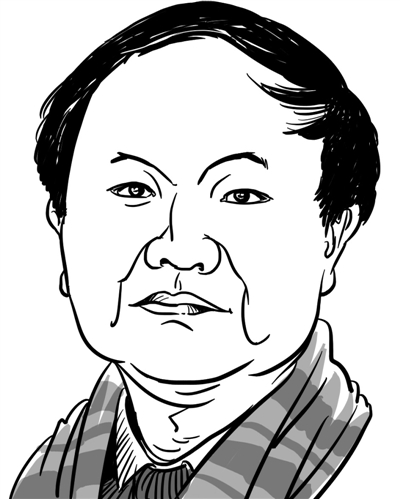-
沒有記錄!
劉慶邦:作家生來就是還淚的
2013/7/24 18:10:20 點擊數(shù): 【字體:大 中 小】
“眼淚不是隨便就能流出來的,每一個作家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是還眼淚的。作品寫完了,作家的眼淚也流干了。”劉慶邦來自河南農(nóng)村,又經(jīng)歷過礦底下的生活磨礪。他自評“情感豐富,意志堅強,但情感卻很脆弱”。
在他看來,天性的善良是成為作家的最根本的條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品中人物的眼淚其實也都是作家的眼淚。”
從1972年開始寫作到現(xiàn)在,40年間,他創(chuàng)作了《斷層》《遠方詩意》《平原上的歌謠》《紅梅》《遍地月光》等7部長篇小說,《走窯漢》《梅妞放羊》《遍地白花》《響器》等30余種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集。這一篇篇、一部部,柔美或酷烈,都是在用眼淚和心血刻畫著鄉(xiāng)土與礦區(qū)人的生命姿態(tài)與情感。
劉慶邦邊從書架上取下一部散文集送給記者,邊解釋道好多書自己也所剩不多,要留著自己看:“有時候我會被自己的作品感動得哭,被眼淚辣得讀不下去……人們總希望看到那些濃烈的東西,其實那些濃烈之底隱藏的依然是樸素。”
230篇:成就“短篇王”
劉慶邦剛剛捧得首屆林斤瀾短篇小說獎。雖然早已將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收入囊中,但被稱為“短篇王”的他依然十分看重這個獎,“獎項的設置本身就體現(xiàn)了文學界對短篇小說的重視。”
眾多學者將他的短篇當做“教科書”。林斤瀾曾評價劉慶邦的小說“來自平民,出自平常,貴在平實,可謂三平有幸”。李敬澤在《鞋》中看到了小說悠遠的文脈,它來自古典傳統(tǒng),經(jīng)過沈從文、汪曾祺等現(xiàn)代作家的反復書寫,同時還包含著自我審視和對古老鄉(xiāng)土的回望。王安憶說,劉慶邦的小說總是有一個懸念,并且他也總不回避困難,有勇氣也有力量開辟這一懸念,將“革命”進行到底……
記者仔細算了一下,劉慶邦已創(chuàng)作了230余篇短篇小說。“很多人對短篇現(xiàn)在的狀況很擔憂,但我一直是持樂觀的態(tài)度。這是寫作的一種生態(tài),它會自然地調節(jié)和平衡。不管是短篇還是長篇,都是一種藝術的轉換。”但他也很納悶:都說現(xiàn)代人沒有時間看書,但調查卻顯示長篇小說的銷路更好。“出版社不愿意出短篇文集,總認為會賠錢,長篇就不至于。很多獎項也沒設短篇獎。無論從輿論引導上還是市場反饋上,人們似乎都更看重長篇。”
在劉慶邦看來,短篇的藝術要求比較高,考量著一個作家的語言駕馭能力和想象力豐富程度,證明著文學藝術性的存在;而長篇滿足的是人們看故事的愿望,這些故事很多是淺層次的,設置一個懸念吊起了人們的胃口,為了知道結果,人們會一個個故事地看下去。這是一種大眾化的閱讀,不是深度閱讀,和看電視劇很相似,不用過腦子,看一個結果就完了。這種閱讀方式也會使長篇小說的市場銷售更好。
魯迅先生寫過中短篇,沈從文、蕭紅的小說大部分也都是中短篇,當代作家汪曾祺、莫言、劉恒最開始都是寫短篇。“特別理解作家寫長篇的愿望。我在寫了很多短篇之后也會想寫長篇。在寫長篇的時候,會有一種放得很開、很過癮、浩浩蕩蕩的感覺,這一點和短篇寫作不太一樣。但不能把長篇作為衡量作家的唯一標準,寫短篇照樣可以出大家。”
“像賽馬一樣,必須要先熱熱蹄子寫短篇,再開始寫長篇。但現(xiàn)在有一些新的作者直接寫長篇,這不太合理。希望他們先從寫短篇開始,這是一種對語言和結構的最基本訓練。”
“寫工人時,一定要超越工作本身”
劉慶邦在礦區(qū)生活了9年,“井下”構成了他創(chuàng)作動機的主要來源。長篇小說《斷層》《紅煤》,《神木》《走窯漢》等11部中篇和上百篇的短篇都在書寫礦工生活。其中《神木》獲第二屆老舍文學獎,據(jù)此改編的電影《盲井》獲第53屆柏林電影藝術節(jié)銀熊獎。
“關注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市場化這一轉型期農(nóng)民工的生存狀態(tài)”是他寫作的定位。在《紅煤》后記中他寫了這樣一句話:“煤礦的現(xiàn)實就是中國的現(xiàn)實。”
劉慶邦不同意將工業(yè)題材作品單獨歸類,認為把工業(yè)生活從車間里脫離出來很重要,不能搞成車間文學。應更多地看到工人身上存在的社會性。工人承載著歷史。但更深層地說是作家要注意到工人豐富的人的特點與情感。具體到某種工業(yè),它會在工人身上打下一種烙印,體現(xiàn)出他的性格上的特點,不必過分強調他的行業(yè)性質。“在寫工人的時侯,一定要超越他的工作本身,把他放到更廣闊的社會空間來考察。寫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情、人性,這樣才能形成文學作品。我頂多寫寫地下的環(huán)境,從來不寫工藝流程。因為這些東西對讀者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他舉《神木》為例,雖然它反映的是礦工生活,但是礦井、煤礦只是一個舞臺和載體。作品著重寫的是人性的扭曲、變異、覺醒和復蘇,但確實又反映了煤礦的特點,工業(yè)背景自然地表露出來,并未過分地強調。
劉慶邦覺得現(xiàn)在工業(yè)題材的淡化反而是文學的一種進步,是對藝術的一種回歸。比如說寫藍領,寫市民,雖沒有貼上工人的標簽,但它實際也是在寫工人的生活,只是將它放到大的社會背景下寫。
“我愿意到小煤礦去體驗生活。因為小的煤礦還是有一定的原始性,工人之間在互相發(fā)生關系。人性還是比較容易表露出來。我可以從宿舍和食堂看出工人之間的關系,寫出他們之間的矛盾和故事。但是在大工業(yè)里工作的工人,下了班以后可能就直接回家了,人性人情都不表露出來,寫的價值不大。”
前年劉慶邦在一個小煤礦的工人宿舍里住了十來天,去食堂排隊買飯,去水很臟的小澡堂洗澡。工人們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持續(xù)寫作就是一個不斷學習的問題,這是一個態(tài)度問題。要保持平常心,把自己隱藏起來,放低姿態(tài)。”
好小說要看“含心量”
“好小說的判斷得從文學的本質來看。小說的本質就是從自己的內心出發(fā),聽從內心的召喚,投入自己的感情,直達人性的深處。從這個意義上講,小說好不好要看小說中包含著作家多少真誠的心靈,也就是‘含心量’。其次就要看小說的情感是否飽滿,能否打動讀者。”劉慶邦將對于情感的衡量放在評判一本小說的中心位置上。“作家要忠于自己的所感所思,才能寫出好的作品。”
情感美是劉慶邦作品美學的核心。他說,文學作品是審美的東西,情感之美應該是美的核心,是中心之美。任何門類的作品,包括文學、影視、曲藝等,都是為了表達人的情感的。這是不管什么時期都不會變的。感動并不是單指讓人流淚,甚至恐懼、震驚等都是感情的一種表達方式,是感情的一種沖擊。但是感情是一定要有的。當然還要有藝術上的形式:情節(jié)的完美、語言的味道、結構的合理等。
心靈化(含心量)、情感的飽滿、情節(jié)、細節(jié)、語言這幾個方面都要恰到好處,是他心目中好作品的標準。
“每個作家在生命深處都是悲涼的、悲痛的,生命就是個悲劇,作品都是表達作家脆弱的感情。真正好的作品,它應該是柔軟的。”
他引用一種極端的說法:“哭泣乃靈氣之謂也”,哭泣有幾分,靈氣就有幾分。哭泣指的就是人的眼淚。因為作家的內心是善良的,敏感的,才能發(fā)現(xiàn)善良,才能對于“惡的東西”感受更強烈。
因為如此,“一個善良的人也許努力之后能成為作家,但是惡人永遠成不了作家。”劉慶邦說,“天性的善良是成為作家的最根本的條件。”在他眼中作家的善良源于天性。作家具有悲憫情懷是因為他們提前看到了生命的盡頭,認識到人生非常短暫和寶貴。于是,對待世界才會有一種包容和善意的態(tài)度。
“我認為文學和宗教之所以一直伴隨著人類,是因為它們能夠使人們產(chǎn)生悲憫情懷和善良的意識。”劉慶邦說。【原標題:劉慶邦:作家生來就是還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