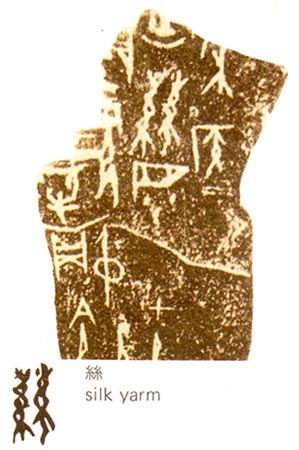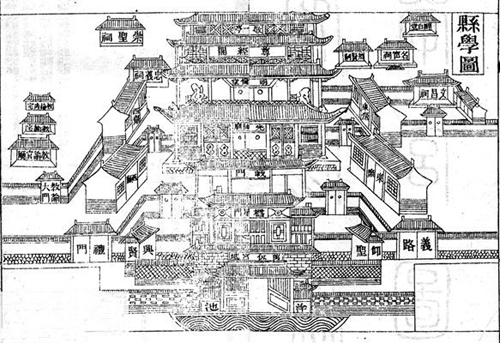-
沒有記錄!
傳乾隆下江南看中安陽美食"三不粘" 御廚帶其回宮
2014/8/4 10:38:05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河南安陽市老城區南關一帶屬宋相州南城的范圍,南關的豆腐腦是安陽有名的民間小吃。老安陽人都說,南關的豆腐腦比別處的香。南關的豆腐腦為什么比其他地方的香?當地人說,跟一段城南舊事有關。
南關豆腐腦
安陽在唐代和宋代時稱相州。
據明嘉靖《彰德府志》記載:宋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增筑相州城,城圍十九里。也就是說,那時的相州城面積比現在的安陽老城大一倍。南關一帶屬宋相州南城的范圍,古相州城的南門,在今南下關的南小門處。南關歷史上有許多民間傳說,當地流傳的豆腐腦的故事,就是源于來鶴樓的往事。
當地人介紹,昔日南關在古相州有“三橋九廟井里碑”之譽。南萬金渠流經南關,南北街道上有座古橋叫井樓橋,來鶴樓邊還有戲樓橋與平橋,戲樓對面有一座火神廟,小井兒的井水清涼甘甜,據說井口是一塊會生長的“活石”,曾有“活石甘泉千家用,車推肩挑半個城”的說法。盛夏時節,常有南關居民推著水車到城里賣水。來鶴樓就建在小井兒之上。
來鶴樓是明代知府陳九紉主持修建的(上世紀60年代初被拆除)。當地百姓傳說,樓建成之日,有仙鶴落在樓頂,故名來鶴樓。來鶴樓的仙鶴南歸后,村民便雕了一只會打鳴報曉的金雞置于樓頂。一天夜晚,這只金雞與賊人搏斗,不幸被殺,且肝腦涂地,于是便有了南關豆腐腦好喝的說法。
當地人流傳的南關豆腐腦另外一個版本跟明朝學者、安陽人崔銑有關。傳說此處原有一座崔銑少年時習文讀書的來鶴亭,亭旁柏樹古井之間有一只報曉雞,后來拆亭建樓時恰好蓋在雞頭之上,把雞腦壓了出來,從此,南關豆腐腦味道鮮美,遠近聞名。
炒三不粘
炒三不粘也是安陽的一道名品,又名“桂花蛋”。
傳說古相州有位縣令,其父喜食花生,但因牙齒脫落,難饗其味,縣令命家廚每天做花生糊、蛋糕供老父食用。時間長了,老人吃厭煩了,家廚便挖空心思不斷變換花樣。有一次,家廚用蛋黃加水、放糖炒了一盤色香味俱佳的炒蛋黃,老人食后大加贊揚。
后來,縣令的父親過七十大壽,壽宴上,自然少不了這道“三不粘”。平時做這道菜的時候,廚師總是用小鍋烹調,一次炒一盤菜。慶賀壽辰這天,吃飯的客人多,小鍋出菜少,廚師就改用大鍋來炒。可是,因為是第一次用大鍋做此菜,該放多少料,廚師的心里沒有底。炒好之后,才發現蛋黃太稀,就連忙往里面添加粉芡,一邊炒一邊往里添油。結果,炒出來的“三不粘”較以往更為油潤光澤、香甜可口,且出鍋時不粘鍋、勺,盛裝時不粘食具,進食時不粘匙、牙,賓客連聲叫絕,后便起名“三不粘”,很快就在安陽聲名鵲起,風行開來。
清乾隆下江南駐蹕安陽時,當地官員向乾隆獻膳,其中就有一道安陽特產“三不粘”。乾隆食后大悅,御廚便將此菜的制作方法帶回宮中。此后,“三不粘”便在宮廷、府衙、市肆、百姓家廣為流傳。
這道菜的制作要旨跟開封的炒紅薯泥很相像,食材極簡,制作卻最見功力。要把蛋黃(紅薯泥)放在炒成的糖汁里,用勺子來回不停地攪勻、淋油,讓糖汁滲進蛋黃(紅薯泥)里,其間,還要根據成色變換火候。如此十分鐘左右才成。
這道名叫“三不粘”的風味小吃從發源于古相州時(唐宋時,安陽被稱為“相州”)算起,至今最少有千年歷史了。一道小吃為什么穿越千年還風行不止?當地人是這么解釋的:“蛋黃好找,可孝心難盡。當年,就是因為那位縣令對老父的一片孝心,才有了這道‘孝心’菜。‘三不粘’的精髓不僅是美味,蘊含的更有中國人修身齊家的入世思想。這是安陽人的驕傲,也是安陽人的節操。”
安陽皮渣
家里的粉條快吃完時,最后總會留下許多碎碎的粉條,扔掉可惜,做成菜又夾不起來,后來,安陽人便想出來一種吃法:將這些碎粉條收集起來,加上其他的配料蒸成碗狀,再切開,或煎、或炸、或炒、或煮、或涼拌,既方便食用,又不浪費,由此還成就了安陽的一道美食:皮渣。
如果還不是特別好理解,那么,這樣解釋吧:安陽皮渣與鄭州、新鄉的民間小食——燜子大致相同,只不過,無論鄭州,還是新鄉街頭,燜子已經越來越少見了。
跟最初的制作理念不同,現在的安陽皮渣大部分用的是完整的粉條批量制作的。煮熟的粉條里加入粉芡、姜絲、白菜葉、肉餡等,攪拌均勻,平鋪在地鍋上,大火蒸上半個小時。剛出鍋的皮渣,濃香軟糯,切下一小塊,就可以直接吃。當然最美味的吃法還是將它切成方塊晾涼,再切成小薄片,拌上辣椒、姜絲、白菜葉醋熘,這樣的美味通常會讓一個花樣般的安陽女孩子一次至少干掉一大盤。
土生土長的安陽人、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新聞學專業三年級學生張娟說:“離開家之后,我也吃過其他城市的炒燜子,但都遠遠不及家鄉的美味、誘人……”
家鄉、血脈
“在如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食物和菜系在文化交流中是一個強大的符號、一種文化的載體,能讓人通過日常的消費不知不覺地感受某種特殊的文化氣氛。當遭遇外來食物時,就必然要在接受和堅持之間作出妥協和調整。”
但一個人哪怕走遍天涯海角,可能最想念的還是家鄉風味的菜肴。
余光中說:“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而今,長大了,鄉愁卻變成了一杯茶、一碗粥和一盤菜,無論時代怎樣變遷,無論血液如何被同化,但骨子里的地域、族群特征、宗親意識,卻隨著年齡的增長、家鄉的漸行漸遠越來越明顯,越來越被強化。
所以,一個在外多年的游子,無論他的口音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無論他的思想發生了何種變遷,可對媽媽那碗粥、家鄉某道菜的執著依舊會凸顯他的家鄉身份。于是,飲食與傳統,就這樣被一代一代地傳下來,并深深地烙上河南印、廣東印以及所有的家鄉印。記者 馬紅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