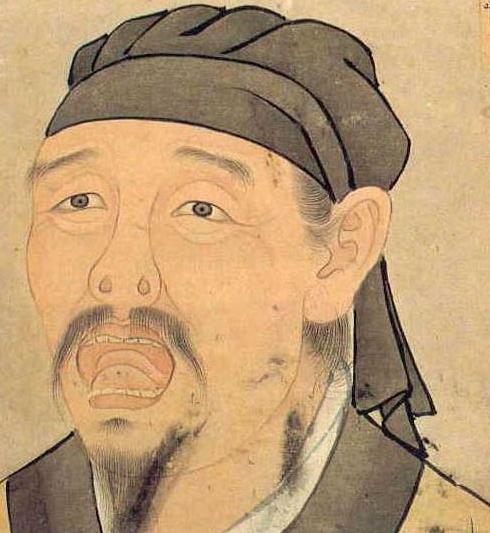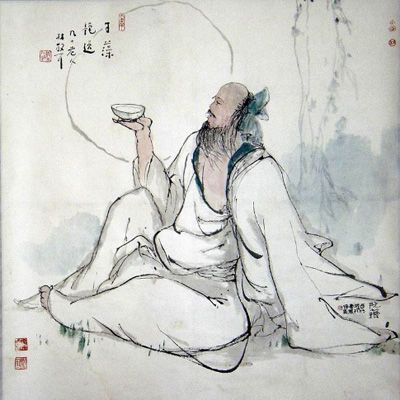精彩推薦
熱點關注
專題推薦
-
沒有記錄!
熱點排行
掙扎于亂世中的悲情蔡文姬(4)
2012/5/8 17:38:03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蔡文姬。朱熹《系辭》云:
《胡笳》者,蔡琰之所作也。東漢文士有意于騷者多已,不錄而獨取此者,以為雖不規規于楚語,而其哀怨發中,不能自已之言,要為賢于不病而呻吟者也。甚至有學者,例如大文豪郭沫若先生認為,“這是一首自屈原的《離騷》以來最值得欣賞的長篇抒情詩,杜甫的《寓同谷縣作歌七首》和它的體裁相近,但比較起來,無論是在量上或是質上都是小巫見大巫的感覺”。郭沫若: 《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報》專刊《文學遺產》。這種觀點非常具有顛覆性,向來在文學史上所占篇幅甚少的蔡文姬,卻被郭沫若提升到與人盡皆知的屈原和杜甫等量齊觀。由此可見蔡文姬的才華越來越受到現當代許多有識之士的關注。
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是一首琴歌,表現了文姬思鄉、離子的凄楚和浩然怨氣。郭沫若稱這首詩“像滾滾不盡的海濤,那像噴發著融巖的活火山,那是用整個的靈魂吐訴出來的絕叫”。郭沫若: 《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報》專刊《文學遺產》。全詩層次清晰,可分兩大層次,前一層次主要傾訴作者身在胡地時對故鄉的思戀;后一層次則抒發出作者惜別稚子的隱痛與悲凄。雖然在傾訴個人的痛苦經歷,可是作者卻有心懷天下的大氣魄,于是從漢末動亂的大現實入筆,而后直切主題,寫到她的被俘,這段經歷對于她來說是刻骨銘心的,在當俘虜的途中她遭受了非人的待遇,隨后她被強留在南匈奴的十二年間,這里沒有漢中平原的優越自然條件,整天出入在“胡風浩浩”、“冰霜凜凜”、“原野蕭條”、“流水嗚咽”之中,異方殊俗的生活是與她格格不入的,思鄉之情油然而生,一切水到渠成,毫無刻意雕琢之痕,渾然天成。我覺得這才是藝術的最高境界,更加值得欽佩的是蔡文姬在敘寫如此悲慘的遭遇時她執著的深情開鑿出一個淡遠深邃的情境:秋日,她翹首藍天,期待南飛的大雁捎去她邊地的心聲;春天,她仰望云空,企盼北歸的大雁帶來的故土的音訊。但大雁高高地飛走了,杳邈難尋,她不由得心痛腸斷,黯然銷魂……這種面對苦難的大度和坦然是堂堂七尺男兒都難以企及的,蔡文姬做到了,所以這首詩不斷被后人傳頌著。從第十三拍起進入了全詩的第二層次,蔡文姬轉入對子女依依惜別之情的描寫,出語便咽,沉哀入骨。千年之后讀來仍然不禁潸然淚下,面對人世間的此種切膚之痛,我無言評說,只好借古人之智慧,宋代范時文在《對床夜話》中這樣說:“此將歸別子也,時身歷其苦,詞宣乎心。怨而怒,哀前思,千載如新;使經圣筆,亦必不忍刪之也。”宋代嚴羽在《滄浪詩話•詩評》中如是品評:“《胡笳十八拍》渾然天成,絕無痕跡,如蔡文姬肝肺間流出。”總之,《胡笳十八拍》既體現了蔡文姬的命薄,也反映出她的才高。蔡文姬創作完《胡笳十八拍》之后,似乎覺得意猶未盡,或許是那段經歷實在太讓人難以釋懷,所以在陳釀一段時日之后,蔡文姬再次以五言體《悲憤詩》抒寫被俘及歸漢的復雜感受。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
逼迫遷舊都,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
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
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撐拒。
此詩以“漢季失權柄”而起,可見漢朝已經覆亡,此時距離那段揪人的經歷已經有些時日,所以這首詩中的情感更加穩定,雖然仍然心中留有余哀,但是如今已安穩地生活在曹操的庇護傘下,也無雷電也無風雨。源于此,這首詩沒有了《胡笳十八拍》中的猶如排山倒海般的情緒傾瀉,只是相對平穩的絮叨。假如說《胡笳十八拍》讀來好像夏日午后里的傾盆大雨,那么這首《悲憤詩》則好比秋后淅淅瀝瀝的綿長陰雨。相同的事件在同一個人的筆下卻能寫出不同的感覺。但是盡管如此,兩首詩中仍然可見同一種創作風格,即那總融入大時代的大氣魄,它們都是以漢朝的命運寫起,從此意義上來說,蔡文姬的這兩首詩不僅僅是個人經歷的抒寫,而且還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因為在詩中反映了漢末戰亂給百姓帶來的不幸。《悲憤詩》作為建安文學最優秀的詩篇之一,受到詩論家的普遍好評。清朝評論家李光地在其《榕村語錄》卷29是這樣說的:蔡文姬《悲憤詩》,纏綿哀怨,立言稱情有體,實開曹杜一派,絕作也。至于騷體《悲憤詩》則普遍被認為是偽作,著名史學家郭沫若《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是這樣論述的:楚歌體的一首可以說是最呆笨、最僵硬,最不切實際的。蔡文姬是被南雄女所掠擄的,而詩中說是“歷險阻兮之羌蠻”。在南雄奴中竟然也有“樂人興兮彈琴箏”。特別是“兒呼母兮啼失笑,我掩耳兮不忍聽”,狀繪得不近乎人情。這首詩倒很有可能是別人造假的。
確實這首騷體《悲憤詩》無論從創作風格、文學水準和歷史事實等方面和前面提到的兩首作品都存在一定的距離。但是并不贊同郭沫若先生因為詩中寫到的臨別掩耳而將其判為偽作。我覺得這樣寫恰恰附和女性的母愛特點,掩耳并非不愿聽子女的悲慟哭聲,而是蔡文姬心中痛苦難忍才不得不言耳,或許只有這樣她才能挪動早已僵硬的雙腿。另外,現中國社科院的徐公持研究員也認為這首詩騷體《悲憤詩》在描寫生動性上稍差。或許之所以無法生動再現歷史場景的癥結在于創作這部作品的人并未親身經歷過。
奉命修史籍 書法傳后人
蔡文姬不僅文學才華卓著,而且記憶力之好可謂無人能比。在前文我們已經提到曹操接蔡文姬歸漢之原因可能出于修史之需要,不管這兩件歷史事件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但是,蔡文姬歸漢后確實奉曹操之命,同時也是繼承父親的遺志,撰寫了《續后漢書》,她可謂對祖國古代文化作出了卓越貢獻。這一事情的來龍去脈在《后漢書》卷84《列女傳•陳留董祀妻》中有比較詳細的記載,一天曹操召見蔡文姬十分客氣地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曹操正襟危坐,表情假裝淡然,其實心中早已迫不及待地想聽到蔡文姬的肯定回答,據載蔡邕在世時,曹操之所以成為蔡府的座上賓,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傾慕于蔡家豐富的藏書,而且曹操重權在握,成為實際上的統治者之后,便將注意力轉向修史事業。文姬臉上略帶謙意地對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余篇耳。”曹操聽此回答幾乎喜出望外,不禁起身大笑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蔡文姬畢竟是出身大戶人家,并沒有受寵若驚,而是在此時刻仍然保持名媛風范,她鎮定自若地說:“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于是接下來的8年間,蔡文姬住在鄴城(今河北省邯鄲市臨漳縣20公里處的鄴鎮)曹操的府邸松濤館,沒有什么特殊需要,幾乎足不出,每天蟄居在一間小屋里,完全沉浸在文字的海洋里,無日無夜,哪怕夜深人靜時,只要腦際突然閃現一段文字,她都會起身挑起夜燈速速記下來,不論酷暑難當,甚或寒氣襲人,蔡文姬完全依靠超強的記憶力和持久恒心整理著父親的藏書,直至回憶、默寫400余篇。在冬寒酷暑中,蔡文姬
《胡笳》者,蔡琰之所作也。東漢文士有意于騷者多已,不錄而獨取此者,以為雖不規規于楚語,而其哀怨發中,不能自已之言,要為賢于不病而呻吟者也。甚至有學者,例如大文豪郭沫若先生認為,“這是一首自屈原的《離騷》以來最值得欣賞的長篇抒情詩,杜甫的《寓同谷縣作歌七首》和它的體裁相近,但比較起來,無論是在量上或是質上都是小巫見大巫的感覺”。郭沫若: 《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報》專刊《文學遺產》。這種觀點非常具有顛覆性,向來在文學史上所占篇幅甚少的蔡文姬,卻被郭沫若提升到與人盡皆知的屈原和杜甫等量齊觀。由此可見蔡文姬的才華越來越受到現當代許多有識之士的關注。
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是一首琴歌,表現了文姬思鄉、離子的凄楚和浩然怨氣。郭沫若稱這首詩“像滾滾不盡的海濤,那像噴發著融巖的活火山,那是用整個的靈魂吐訴出來的絕叫”。郭沫若: 《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報》專刊《文學遺產》。全詩層次清晰,可分兩大層次,前一層次主要傾訴作者身在胡地時對故鄉的思戀;后一層次則抒發出作者惜別稚子的隱痛與悲凄。雖然在傾訴個人的痛苦經歷,可是作者卻有心懷天下的大氣魄,于是從漢末動亂的大現實入筆,而后直切主題,寫到她的被俘,這段經歷對于她來說是刻骨銘心的,在當俘虜的途中她遭受了非人的待遇,隨后她被強留在南匈奴的十二年間,這里沒有漢中平原的優越自然條件,整天出入在“胡風浩浩”、“冰霜凜凜”、“原野蕭條”、“流水嗚咽”之中,異方殊俗的生活是與她格格不入的,思鄉之情油然而生,一切水到渠成,毫無刻意雕琢之痕,渾然天成。我覺得這才是藝術的最高境界,更加值得欽佩的是蔡文姬在敘寫如此悲慘的遭遇時她執著的深情開鑿出一個淡遠深邃的情境:秋日,她翹首藍天,期待南飛的大雁捎去她邊地的心聲;春天,她仰望云空,企盼北歸的大雁帶來的故土的音訊。但大雁高高地飛走了,杳邈難尋,她不由得心痛腸斷,黯然銷魂……這種面對苦難的大度和坦然是堂堂七尺男兒都難以企及的,蔡文姬做到了,所以這首詩不斷被后人傳頌著。從第十三拍起進入了全詩的第二層次,蔡文姬轉入對子女依依惜別之情的描寫,出語便咽,沉哀入骨。千年之后讀來仍然不禁潸然淚下,面對人世間的此種切膚之痛,我無言評說,只好借古人之智慧,宋代范時文在《對床夜話》中這樣說:“此將歸別子也,時身歷其苦,詞宣乎心。怨而怒,哀前思,千載如新;使經圣筆,亦必不忍刪之也。”宋代嚴羽在《滄浪詩話•詩評》中如是品評:“《胡笳十八拍》渾然天成,絕無痕跡,如蔡文姬肝肺間流出。”總之,《胡笳十八拍》既體現了蔡文姬的命薄,也反映出她的才高。蔡文姬創作完《胡笳十八拍》之后,似乎覺得意猶未盡,或許是那段經歷實在太讓人難以釋懷,所以在陳釀一段時日之后,蔡文姬再次以五言體《悲憤詩》抒寫被俘及歸漢的復雜感受。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
逼迫遷舊都,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
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
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撐拒。
此詩以“漢季失權柄”而起,可見漢朝已經覆亡,此時距離那段揪人的經歷已經有些時日,所以這首詩中的情感更加穩定,雖然仍然心中留有余哀,但是如今已安穩地生活在曹操的庇護傘下,也無雷電也無風雨。源于此,這首詩沒有了《胡笳十八拍》中的猶如排山倒海般的情緒傾瀉,只是相對平穩的絮叨。假如說《胡笳十八拍》讀來好像夏日午后里的傾盆大雨,那么這首《悲憤詩》則好比秋后淅淅瀝瀝的綿長陰雨。相同的事件在同一個人的筆下卻能寫出不同的感覺。但是盡管如此,兩首詩中仍然可見同一種創作風格,即那總融入大時代的大氣魄,它們都是以漢朝的命運寫起,從此意義上來說,蔡文姬的這兩首詩不僅僅是個人經歷的抒寫,而且還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因為在詩中反映了漢末戰亂給百姓帶來的不幸。《悲憤詩》作為建安文學最優秀的詩篇之一,受到詩論家的普遍好評。清朝評論家李光地在其《榕村語錄》卷29是這樣說的:蔡文姬《悲憤詩》,纏綿哀怨,立言稱情有體,實開曹杜一派,絕作也。至于騷體《悲憤詩》則普遍被認為是偽作,著名史學家郭沫若《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是這樣論述的:楚歌體的一首可以說是最呆笨、最僵硬,最不切實際的。蔡文姬是被南雄女所掠擄的,而詩中說是“歷險阻兮之羌蠻”。在南雄奴中竟然也有“樂人興兮彈琴箏”。特別是“兒呼母兮啼失笑,我掩耳兮不忍聽”,狀繪得不近乎人情。這首詩倒很有可能是別人造假的。
確實這首騷體《悲憤詩》無論從創作風格、文學水準和歷史事實等方面和前面提到的兩首作品都存在一定的距離。但是并不贊同郭沫若先生因為詩中寫到的臨別掩耳而將其判為偽作。我覺得這樣寫恰恰附和女性的母愛特點,掩耳并非不愿聽子女的悲慟哭聲,而是蔡文姬心中痛苦難忍才不得不言耳,或許只有這樣她才能挪動早已僵硬的雙腿。另外,現中國社科院的徐公持研究員也認為這首詩騷體《悲憤詩》在描寫生動性上稍差。或許之所以無法生動再現歷史場景的癥結在于創作這部作品的人并未親身經歷過。
奉命修史籍 書法傳后人
蔡文姬不僅文學才華卓著,而且記憶力之好可謂無人能比。在前文我們已經提到曹操接蔡文姬歸漢之原因可能出于修史之需要,不管這兩件歷史事件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但是,蔡文姬歸漢后確實奉曹操之命,同時也是繼承父親的遺志,撰寫了《續后漢書》,她可謂對祖國古代文化作出了卓越貢獻。這一事情的來龍去脈在《后漢書》卷84《列女傳•陳留董祀妻》中有比較詳細的記載,一天曹操召見蔡文姬十分客氣地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曹操正襟危坐,表情假裝淡然,其實心中早已迫不及待地想聽到蔡文姬的肯定回答,據載蔡邕在世時,曹操之所以成為蔡府的座上賓,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傾慕于蔡家豐富的藏書,而且曹操重權在握,成為實際上的統治者之后,便將注意力轉向修史事業。文姬臉上略帶謙意地對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余篇耳。”曹操聽此回答幾乎喜出望外,不禁起身大笑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蔡文姬畢竟是出身大戶人家,并沒有受寵若驚,而是在此時刻仍然保持名媛風范,她鎮定自若地說:“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于是接下來的8年間,蔡文姬住在鄴城(今河北省邯鄲市臨漳縣20公里處的鄴鎮)曹操的府邸松濤館,沒有什么特殊需要,幾乎足不出,每天蟄居在一間小屋里,完全沉浸在文字的海洋里,無日無夜,哪怕夜深人靜時,只要腦際突然閃現一段文字,她都會起身挑起夜燈速速記下來,不論酷暑難當,甚或寒氣襲人,蔡文姬完全依靠超強的記憶力和持久恒心整理著父親的藏書,直至回憶、默寫400余篇。在冬寒酷暑中,蔡文姬
責任編輯:C009文章來源:中國崛起網
相關信息
沒有記錄!
精彩展示
沒有記錄!
評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