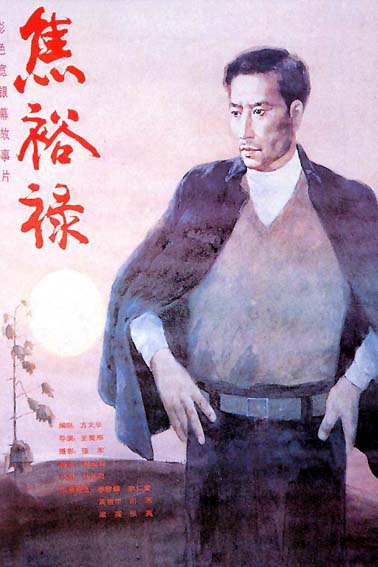精彩推薦
熱點關注
專題推薦
-
沒有記錄!
熱點排行
大相國寺記
2014/2/21 12:32:04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開封城里有座大相國寺。
我和琳被擠在小巴士的一角落里,離開朱仙鎮一個多小時后,終于回到了開封,進了相國寺汽車站。這時,天空飄起了淅淅瀝瀝的雨滴,我頂著地圖,拉著琳琳拐進了左近的一條巷子。好一條飄著酒飯香氣的老街,低矮的屋檐下,一屜屜包子堆得跟小山似的。于是我們隨便撿了一家,要了足足三屜的小籠包。
二屜包子下肚后,心滿意足的我,抹了抹嘴上的油開始和小店老板聊起天來。原來傳說中的大相國寺就在不遠處的前方,而這條不起眼的小街,也有著一個香艷的名子——胭脂河街。遙想“四水貫都”的日子里,一條彎彎的小河在門前流過,趙師師、錢師師、孫師師們云髻水袖,嫣嫣然地從河邊飄過,落下的點點水粉把這河都染成胭脂的顏色,那是怎一番的風情。滄海桑田過后,我們沿著這依然飄著香的小巷走到了盡,大相國寺在一片熙攘繁華之中,與我們相逢了。
古寺紅塵
在我的思想之中,古寺名藍總是與明山凈水、深山老林聯系在一起的,似乎只有遠離世間的滾滾紅塵,長伴青燈古卷,才會四大皆空,修成正果。不想大相國寺卻棲身于市井,與酒肆屠戶為鄰,與販夫走卒為伍,著實讓我大感意外。廟的東墻之外,行人如織、店鋪林立,那是號稱“開封的王府井”的馬道街;西邊更甚,一個巨大的農貿市場整個壓了過來了,大有一口吞相國寺面而后快勢頭。于是不禁為僧人們擔起心來,不知這大相國寺一代代的高僧們是如何在這樣喧鬧的叫賣聲中,敲打著木魚,聆聽著佛音,修行著、思考著、歷練著的。
看了書才知道,大相國寺的熱鬧與嘈雜是由來已久的。宋人在《燕翼貽謀錄》就有這樣的描述:“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于此。” 《東京夢華錄》里更是詳細地描述了“相國寺每月五次開放萬姓交易”的盛況,凡是市面上流通的服飾、文具、藥物、日常生活用品等等,幾乎都可以買到,而且,有許多東西甚至是獨此一家,別無分號的。
不僅老百姓經常光顧,就連皇親國戚、達官貴人也常在這里流連忘返,黃庭堅就曾在這里買到過史學家宋祁的《唐史稿》手稿。 傳說,在長年在開封居住的李清照一有空閑就拉丈夫到大相國寺去逛街。她老公趙明誠可是想當年著名的文物鑒定家(曾多次擔任“鑒寶”節目嘉賓),于是夫妻倆到了大相國寺,不去參禪拜佛,老婆跑著去買零食,她在自己的書里就曾介紹當年喜歡的零食“炒銀杏、栗子、河北鵝梨、梨條、梨干、梨肉、膠棗、棗圈、梨圈、桃圈、核桃、肉牙棗、海紅嘉慶子、林檎旋烏李……”怎么樣,流口水了吧。老公呢?南邊大樹下邊,拿個放大鏡,正在一大堆舊書舊畫古董之間流連呢。每每太陽落山時候,李MM和趙GG才抱著一大堆書畫,提著一大包零食,手拉手,一步一回頭的告別大相國寺。
到了民國的時代,人家馮玉祥將軍更爽快,干脆就把大相國寺改成了中山市場。
所謂“佛不避世”,大概就是此理。
始建相國寺
話扯遠了,回到相國寺。想進寺廟,門票三十,一分都不能少。邁進山門,開始說說大相國寺的歷史:大相國寺始建于北齊天保六年(公元555年),一代梟雄高洋登基后駕游汴州,憑吊信陵君的故跡,深感公子高義,并詔敕在魏信陵公子的故宅上建“建國寺”以示紀念。 隨后,唐代大書法家李邕在《大相國寺碑》中記載“建國寺”更名為大相國寺的原因:傳說唐睿宗李旦曾在夢中遇到了金身彌勒,因而,由“相王”而登基做了皇帝,故“改故建國寺為大相國寺”以紀之。 從此,大相國寺之名沿用至今。
《西游記》也有一個關于大相國寺建寺的傳說:一次,唐太宗去陰曹地府觀光考察時,借得開封府一個名叫相良的人在陰間存放的金銀,才得以生還。返回人間后,唐太宗去找相良還錢,但這個販賣烏盆瓦器相良卻說什么也不肯收這筆錢,唐太宗怕自己失了誠信,只好用這金銀在開封建了座寺廟,也就是今天的大相國寺了。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就是由此而始。故事雖不可信,但也給大相國寺加重了幾筆神話的色彩。
到了北宋,大相國寺進入了香火鼎盛時期。宋太祖、宋太宗都對相國寺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建,這里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佛教道場。那時,相國寺占地五百四十多畝(相關于今天相國寺的二三十倍),分為六十四個禪院,殿宇高大無比,壯麗絕倫,古人稱贊其“大相國寺天下雄”。北宋大相國寺號稱 “皇家禪院”,一代代的帝王多次巡幸,皇帝生日時,文武百官要到寺內設道場祝壽,重大節日,祈禱活動也多在寺內舉行,新科進士題名刻石于相國寺為北宋慣例。寺院著名的和尚都獲得過皇帝賜封號的榮譽。世界上第一個醫用人體模型“針灸銅人”也存放在大相國寺的仁濟殿中一百多年,供世人瞻仰,于是有了“資圣熏風”汴梁名勝。
“花和尚”與佛
邁進大相國寺的山門,直面迎客的不是哼哈二將,不是笑彌勒,而是“倒拔垂楊柳的魯智深”。 如果說海天佛國的普陀山那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初祖達摩修行在少林,濟公和西湖靈隱寺“沾親”是合情合理,那找“平生不修善果,只愛殺人放火”花和尚來當大相國寺的形象代言人是不是就有點說不過去了?這不是要活活氣煞大相國寺千多年來的苦苦修行的各位高僧了?別人不說,琳就死活不愿與其為伍,說什么也不和“花和尚”合影,理由是他太丑,于是換了我當模特。我卻是從小就喜歡魯智深的,有機會和他合個影,自然快活,快步上前,抱了他的大腿,留了個念想。
魯智深以其:愛打報不平、率性而為、殺人如麻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智深有一身勇力,卻不曾行欺壓良善之事,不拘禮法,卻不能容他人橫行。歷來對魯智深最為推崇的是晚明大思想家李贄,他說智深是“大慈大悲的羅漢菩薩佛”, 說他從不守佛門之規矩,從不念念成佛,一如維摩詰,“煩惱即菩提,不離生死而住涅槃結果”,于是他倒真成佛了。無怪金圣嘆老爺子都說他是“上上人物”。 而一句“罷,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到讓《紅樓夢》里典型的淑女薛寶釵與這萬里隨緣化的“花和尚”,有了共鳴,確是妙事。
而智深和為他剃度他出家的智真長老的一次對話,又讓人真真感到了禪宗佛性中悟的一面。長老只一句:“徒弟一去數年,殺人放火不易!” 智深因而得法,才說出:“平生不修善果,只愛殺人放火。忽地頓開金枷,這里扯斷玉瑣。咦!錢塘江上潮信來,今日方知我是我” 的偈子。
責任編輯:C005文章來源:開封旅游網 2009-2-20
相關信息
沒有記錄!
著名人物
沒有記錄!
精彩展示
沒有記錄!
評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