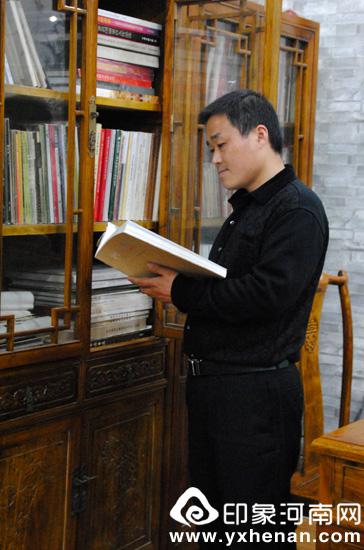-
沒(méi)有記錄!
熔古鑄今 邃密精深——評(píng)《杜甫全集校注》
2014/12/15 8:55:28 點(diǎn)擊數(shù): 【字體:大 中 小】
杜甫是我國(guó)古典詩(shī)歌巔峰時(shí)期的代表人物,他關(guān)心國(guó)政民情,詩(shī)風(fēng)沉郁頓挫,被尊為“詩(shī)圣”。自詩(shī)人去世之后,人們便開(kāi)始了杜詩(shī)的整理注釋工作,至宋代就有“千家注杜”之說(shuō),涌現(xiàn)了一批重要注杜學(xué)者。到清代前中期,杜詩(shī)的整理和研究再次進(jìn)入高峰,錢謙益的《錢注杜詩(shī)》,仇兆鰲的《杜詩(shī)詳注》,楊倫的《杜詩(shī)鏡銓》,等等,可謂碩果累累。在此之后200余年,并未出現(xiàn)箋注杜甫全集之作。由已故著名學(xué)者蕭滌非領(lǐng)銜主編,歷經(jīng)36年打磨的《杜甫全集校注》今年由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堪稱杜集整理史上的集大成之作。其成績(jī)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gè)方面。
第一,校勘精密,辨?zhèn)螌徤鳌N谋拘?迸c辨?zhèn)问枪偶淼幕A(chǔ),宋人整理杜集的最大特點(diǎn)是以嚴(yán)格、精審、全面為后人讀杜奠定良好的基礎(chǔ)。本次以明末毛晉抄補(bǔ)《宋本杜工部集》為底本,校以十三種宋元刻本和一種明抄本,又以宋刊《太平御覽》《文苑英華》《樂(lè)府詩(shī)集》等類書、總集參校,充分利用宋代留存的文獻(xiàn),努力呈現(xiàn)杜甫作品的原貌。
第二,體例完備,內(nèi)容豐富。別集箋注發(fā)軔于宋代,杜集箋注在別集箋注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宋人編撰杜集著作仍較簡(jiǎn)略,有關(guān)箋注體例和內(nèi)容的安排仍然處于探索階段。清人也大多選擇偏重某一方面,不以全備為目標(biāo),即使是仇兆鰲,雖以“詳注”名書,卻也自覺(jué)地放棄了“與杜為敵”的意見(jiàn)。可見(jiàn)全面汲取前人的成果并不容易。箋注體例看似簡(jiǎn)單,實(shí)在關(guān)乎著述宗旨和研究心得的呈現(xiàn)。匯聚歷代注杜成果于一書,《杜甫全集校注》以此為目標(biāo),在體例上集合舊例,創(chuàng)設(shè)新目:題解、注釋、集評(píng)、備考、校記、附錄,尤其是集評(píng)、備考兩項(xiàng),集歷代評(píng)議,備諸相左觀點(diǎn),綱舉目張,幾乎網(wǎng)羅了千年來(lái)人們有關(guān)杜甫作品的各種意見(jiàn),解決了古來(lái)杜注中未能妥善處理的問(wèn)題,基本達(dá)到了一編在手、縱覽無(wú)遺的目標(biāo)。
第三,別擇精審,考按合理。宋人說(shuō)杜詩(shī)“無(wú)一字無(wú)來(lái)處”,自此而后,歷代注家大多廣征遠(yuǎn)引,務(wù)求博雅,有的甚至偽造箋注,如“偽王注”“偽蘇注”,有的則附會(huì)史實(shí),穿鑿支離,紛挐不清。本書參閱杜集評(píng)注本130余種,卻能刪削得當(dāng),條理分明,如注釋部分,力求“詞語(yǔ)明而詩(shī)義彰”,遇到眾說(shuō)紛紜時(shí),去蕪存菁,然后以按語(yǔ)揭明己見(jiàn),其存疑存異的內(nèi)容則附入“集評(píng)”“備考”。
第四,考訂精確,論述平實(shí)。《校注》在全面汲取舊注的基礎(chǔ)上,充分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糾正舊注之訛,提升箋注水平。如辨杜甫最后漂泊湖南的詩(shī),舊注將《入喬口》《銅官渚守風(fēng)》《雙楓浦》《發(fā)潭州》等置于《宿花石戍》《次晚洲》諸詩(shī)之后,其實(shí)是時(shí)間上前后顛倒了,于此,《校注》者根據(jù)實(shí)地踏勘的成果做了調(diào)整,澄清了千百年的沿襲之誤。
《杜甫全集校注》作為一部守正出新之作,其完備周到的體例、精深邃密的治學(xué)精神,對(duì)當(dāng)今古籍整理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作者:李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