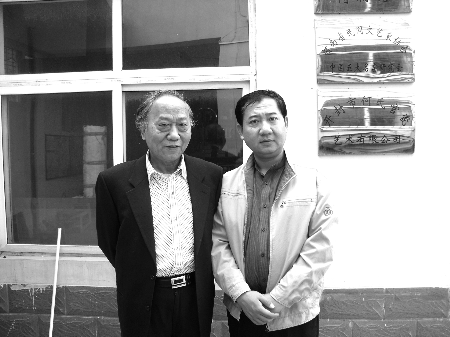精彩推薦
熱點關注
專題推薦
-
沒有記錄!
熱點排行
包公“龍馬負圖處”碑是開封華夏文明的見證
2013/4/12 9:30:34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開封北大寺有一方包拯“龍馬負圖處”碑(以下簡稱“包拯碑”),碑中承載著華夏“河圖”文化發源地和包拯時期宋代文化的重要信息。一個時期以來,圍繞“包拯碑”真偽問題形成了“認可派”與“疑偽派”之爭。現根據自己掌握的歷史資料,談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疑偽派”認為清代江蘭偽造“包拯碑”的理由
據有關史料記載,開封北大寺“包拯碑”發現于清代乾隆五十年,即公元1785年,河南布政使(相當于省級行政官)江蘭在開封市郊黑崗口修堤時掘出此碑,并建祠蓋亭加以保護。后來祠亭圮廢,被人遷入寺內。
“疑偽派”學者認為,“龍馬負圖處”的地點在洛陽孟津縣,不在開封,歷史早有的定論。宋代龍圖閣直學士包拯明知此事,不會為開封題寫“龍馬負圖處”的碑文。因而懷疑“包拯碑”是河南布政使江蘭偽造。同時又認為,即使此碑是包拯題寫,也應是從洛陽孟津移到開封來的。
為了說明河南布政使江蘭有偽造“包拯碑”的動機,“疑偽派”學者引用了開封《祥符縣志》記載,說:江蘭任職期間,開封府風不調雨不順,乾隆“四十九年不雨,至五十年春多暴風揚沙,大旱禾盡,秋冬大饑”。于是便推測,在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江蘭可能產生了借“龍馬”神威和包拯英名偽造“包拯碑”的想法,以達到安撫開封百姓,保持社會穩定的目的。
盡管“疑偽派”學者也承認,目前還沒有掌握“包拯碑”不是包拯手跡的證據,但又明確表示出不認可態度,說這“是個不解之謎”。
我們認為,“包拯碑”所承載的信息十分重要,不僅僅事關宋代包拯手跡本身的真偽問題,還事關開封是否為上古時期華夏“河圖”文化發源地等重要歷史文化傳承問題。如果冒然采取“疑偽”的態度來對待,將會使“包拯碑”承載的厚重華夏文化價值大打折扣,其負面影響不言而喻。
我們無意為爭奪華夏“河圖”文化發源地資源,違背客觀歷史事實,決意把“包拯碑”說成是包拯手跡。但如若“包拯碑”果真是包拯手跡,卻被蒙上了不白之冤,恐怕也非“疑偽派”的本意。所以,客觀論證“包拯碑”真偽,對發掘、傳承開封華夏和大宋文化既十分必要,又意義深遠。
二、“包拯碑”是宋代包拯手跡的幾個理由
包拯圖像
(一)開封是“龍馬負圖”最早發源地之一。
“龍馬負圖”,也稱“神龜負圖”。據西周文王《周易•系辭上》記載:“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西漢經學家孔安國在解釋《尚書•顧命》中說:“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其中“伏羲”,是上古時期炎黃的先祖,也稱“天皇”,或“天王”;“龍馬”,傳說是“天地”間的精靈,也有人認為它是河馬、犀牛一類大型水中動物;“河圖”,是“龍馬”,或“神龜”背部自然形成的圖案。傳說伏羲通過對圖案認真觀察和對自然界事物的認識,發現了日月星辰運轉,季節氣候變化,草木興衰等規律的“八卦”圖,古代天文、地支、歷法、中醫、算數、宗教等文化的“根”都源自“河圖”。
“河圖”并非僅僅發源于洛陽孟津一帶,古籍中也多有“河圖”與開封相關的記載。人文始祖倉頡帝都在開封夷門一帶,漢代緯書《春秋元命苞》記載說:倉頡“受河圖綠字,于是窮天地之變化。仰觀奎星圓趨知勢,俯察龜文鳥語山川,指掌而創文字”;黃帝姬芒即位于開封軒轅丘(樓),魏國史官《竹書紀年》記載說:黃帝即位后,“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虞舜時期,大禹在開封浪蕩渠、龍門等地治水時,靠著三件珍寶,第一件便是河伯授給的“河圖”。
后人認為,“龍馬負圖”一般出現在孟津上游的洛水、伊水、龍門地區,開封不在其中。但是,這一定論也值得斟酌,因為開封一帶也有洛水、伊水、龍門的歷史記載。
據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記載:浪蕩渠“其水上承陂水,東北逕雍丘(杞縣)城北。又東分為兩瀆,謂之雙溝,俱入白羊陂。陂水東合洛架口,水上承汳水,謂之洛架水,東南流入于睢水”。還記載:“汳水又東,龍門故瀆出焉。瀆舊通睢水,故《西征記》曰:龍門,水名也。門北有土臺,高三丈余,上方數十步。汳水又東徑濟陽考城縣故城南,為菑獲渠。”其中“浪蕩渠”、“睢水”、“汳水”就是“汴水”,也稱“洛架水”,或“洛水”。“洛水”與“龍門”都在大禹治水的杞縣北部偏東一帶,這也是商、周王朝均將夏禹后裔封在杞國的重要原因。清代《陳留縣志•山川》和《河南通志•開封府》均記載:“伊水(現稱圈章河),在陳留東北二十里,環繞伊尹故里。”可見,伊水和商代伊尹故里也在開封陳留一帶。
開封一帶的陳留倉頡“河圖村”、陳橋驛黃帝“風凰臺”、杞縣大禹“龍門”治水,自古以來就有歷史傳承,也為宋代龍圖閣直學士包拯在開封題刻“龍馬負圖處”碑提供了歷史文化依據。因此,“包拯碑”不在開封,或移自洛陽孟津的揣測和“歷史定論”,難以讓人信服。
(二)開封倉頡廟“包拯碑”江蘭“偽造”前就存在。
1042年(左)與1057年(右)包拯石刻對比圖
從“疑偽者”的論據和觀點分析,其掌握的歷史資料多為清代河南布政使江蘭在開封黑崗口掘石建祠時期。僅從這些資料分析歷史事件,也難免具有局限性。其實,關于“包拯碑”的來歷還有一種說法。
前一時期,我們了解到:開封市臺聯王麗娜會長至今仍保存著祖父王潤堂抄錄的《河南日報》史料一份。據該史料顯示,1957年2月10日,一位叫李村人的學者在《河南日報》《一些歷史人物的墓地》一文中寫道:“在開封倉頡墓旁的廟內,從前有包拯所寫的‘龍馬負圖處’五個大字石刻橫匾。”可見,倉頡廟里的“石刻橫匾”,就是清代河南布政使江蘭黑崗口發現的“包拯碑”。
遺憾地是,到了公元1652年(清順治九年),河南知府朱之瑤在開封西雞兒巷東部主持建造文廟時,將坐落在開封東北5公里劉莊天主教堂一帶的倉頡廟拆除了,現有開封文廟的部分倉頡廟磚瓦木料原物可以作證。朱之瑤建造開封文廟的時間,距離公元1642年明代(崇禎十五年)李自成率農民起義軍攻打開封,官軍扒開黃河抵御起義軍,導致開封慘遭淹沒的歷史不過十年。此時的開封一派凄涼,物質匱乏,朱之瑤只好采取“拆東墻補西墻”的方法來解決開封文廟建設之急需,結果不知倉頡廟內有多少如同“包拯碑”一樣的碑文被遺棄。
朱之瑤建造文廟,祭祀圣人孔子有功;而拆除倉頡廟,褻瀆人文始祖神靈則有過。功也罷,過也罷,朱之瑤早已出世托生,但卻為我們留下了一道追尋“包拯碑”蹤跡的難題。
所幸難題終于有了答案:即使從公元1652年朱之瑤拆除倉頡廟算起,“包拯碑”出現的時間,至少要比公元1785年江蘭掘出此碑早130多年。如果李村人先生沒有像河南布政使江蘭一樣“偽造”歷史,那么宋代包拯在開封題刻“龍馬負圖處”碑的歷史就應該是真實的。
(三)清代江蘭偽造“包拯碑”的理由不成立。
上述事實表明,一些既不科學又不嚴謹的所謂“歷史定論”,確實給后人研究歷史帶來了很大欺騙性。就像黃帝帝都“軒轅丘”早有定論在新鄭一樣,至今仍以歷史玩笑的形式讓世代黃帝子孫為之傾倒和膜拜。當然,這也為后人留下很多破綻和重新審視客觀歷史的諸多理由。
因此,“疑偽”本身不是問題,而且對那種敢于向欺騙性“歷史定論”說“不”的精神,理應予以鼓勵才是。問題在于“疑偽者”提出清代江蘭偽造“包拯碑”的一些理由,經不起歷史推敲。
比如,“疑偽者”認為,龍圖閣直學士包拯既然知道“龍馬負圖處”的地點在洛陽孟津,是不會在開封題寫“龍馬負圖處”碑文的。因此,碑文不是包拯題寫。
假如用同樣的道理,來為河南布政使江蘭做辯護,也同樣會得出江蘭不可能偽造“包拯碑”碑文的結論。
試想,清代的江蘭,曾分別于公元1779年至1780年(乾隆44年-45年)、公元1782年至1786年(乾隆47年-51年)、公元1786年至1788年(乾隆51年-53年)三任河南布政使,歷時約8年,期間還曾負責黃河道的治理工作,且又擔任過清朝大理寺少卿、太仆寺卿、河南巡撫、山東布政使、河東河道總督、兵部左右侍郎等要職,難道他不知道“龍馬負圖處”的地點在洛陽孟津嗎?既然知道,即使他有偽造“包拯碑”的賊心,還敢有冒著被世人恥笑風險的賊膽嗎?
所以,“包拯碑”不是河南布政使江蘭造假,而是源自包拯題文碑刻和開封華夏人文資源的歷史傳承。河南清代老長官江蘭確有蒙受不白之冤的可能,而我們卻沒有資格下紅頭文件平反昭雪,只好以此文勸其在天之靈想開一些,哪個廟里沒有屈死的鬼呢?
北大寺“包拯碑”位置圖
北大寺坐落在夷門山鐵塔的西南隅,從地理位置分析,這里應歸屬公元291年,即西晉元康元年誕生中國第一部漢字佛經《放光般若經》的水南寺。當時北大寺是翻譯佛經的西域高僧無叉羅、竺叔蘭、竺法寂等獨身者的居院,后人俗稱為“獨居寺”。公元729年,唐代(開元十七年)玄宗東游至此,改名為“封禪寺”,以表彰西域高僧翻譯般若學說做出的重大貢獻。北宋改稱“開寶寺”。
北大寺西南部有地名稱“北倉”,自古就是倉頡后裔“倉”氏生活的聚集地。后來,這里演變成了倉氏族人祭祀倉頡的寺廟,并與開寶寺分為兩地。或許正是居住在這一帶的倉頡后裔,將“包拯碑”搬遷到北大寺內保護起來。這不僅是保護倉姓始祖倉頡廟內的圣物,也是出自于對包拯的愛戴和崇敬。
三、“包拯碑”內涵與開封歷史文化一脈相承。
“包拯碑”的核心內容,源自對華夏文化精髓“龍(河)圖”的認可和追記;立碑形式本身,也體現了大宋文化對上古時期華夏文化精髓的傳承和弘揚。“包拯碑”提示后人:即便是豐富深厚的大宋文化,也是自上古時期“龍(河)圖”文化傳承發展而來的,兩者可以相互印證歷史,卻不能將歷史割裂開來。
開封歷史文化發展的脈絡,證實了這一認識的客觀性。無論“三皇五帝”時期出現的“河圖洛書”,或是宋代著名易學大師陳摶發現的先進文化成果“河圖”圖形列式、秦九韶創作的《數術九章》;無論是宋真宗直接策劃和領導的“天書祥符”運動,或是宋徽宗親自指導、張擇端首創的“清明上河圖”,無不打上了繼承和弘揚華夏文化“河圖”的歷史烙印,只是需要我們剔去糟粕,保留精華,發揚光大而已。
直到現在,人們仍然把學習、傳承文化知識的工具和載體用“圖書”來稱呼。其實,“圖書”二字就是“河圖”之“圖”和“洛書”之“書”的簡稱。自上古時期以來,不管“河圖洛書”的形式、內容、傳承方式等如何演變,可作為記錄和傳播先進文化載體的基本功能卻沒有改變,直到現在仍在不斷創新發展著。
在國務院把河南打造為“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發展戰略指導下,開封正在搶抓機遇,大力開展國際旅游名城建設工作。為此,深入發掘和開發“包拯碑”佐證的開封華夏人文歷史資源,用這些資源來烘托和提升大宋文化的層次與內涵,加快開封華夏文化旅游聚集地建設,提高開封文化旅游資源在國際客源地的吸引力和競爭力,促進開封文化旅游發展再上新臺階,都很有意義。
北大寺“包拯碑”保存至今,對印證開封深厚的華夏文明和發掘人文資源,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幸事。
責任編輯:C006文章來源:議政網 2012-03-21 作者:韓鵬
相關信息
沒有記錄!
著名人物
沒有記錄!
精彩展示
沒有記錄!
評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