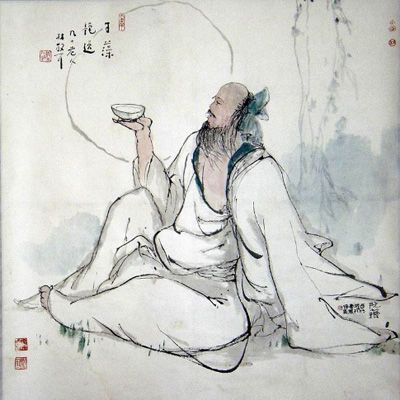精彩推薦
熱點關注
- 1、一紙“勸進文”逼死了阮籍
- 2、被出賣的黃樵松將軍
- 3、別樣教育 創出奇跡——陳省華的教子之
- 4、"一毛不拔"的楊朱
- 5、董宣用計囚國舅
- 6、宋太祖千里送京娘非虛構 對美女動心為
- 7、種世衡的妙計
- 8、“另類老師”邊韶
專題推薦
-
沒有記錄!
熱點排行
李綱與蔡京父子關系考辨
2014/12/4 9:05:33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關 鍵 詞:李綱 徽宗內禪 蔡氏父子
作者簡介:王晴,浙江大學出版社編輯。
李綱(1083—1140),字伯紀,邵武(今屬福建)人,是南宋初第一任宰相、南北宋之交重要的抗金歷史人物。但與生活在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突出、黨爭激烈的這一時期很多重要人物一樣,李綱也有著復雜的人際關系,其與蔡氏(京、攸)的關系就十分微妙,成為當時政敵對其攻擊的炮彈。本文試對此問題作一番考察分析,不當之處,請批評指正。
一、李綱由蔡氏薦引
蔡京、蔡攸歷來被看作是導致靖康之難的罪人。特別是蔡京,在徽宗朝四度任相,排斥異己,汲引同類,“二紀之間,門生故吏,充初天下”①。當時臣僚對李綱與蔡氏關系的彈劾主要集中在三點:一是指稱李綱由蔡氏引用,“平時諂事蔡京、蔡攸”,“卵翼于蔡氏之門,傾心死黨”②,朱勝非在《秀水閑居錄》中說李綱乃“蔡京之子攸黨也”③,宋廷在回答金朝楊天吉等問罪結交余祝的回書中,也稱吳敏、李綱“元乃蔡京、蔡攸之黨”④;二是謂當徽宗內禪之際,李綱受蔡攸指使,上書乞徽宗傳位,“逮上皇(徽宗)將有內禪之意,攸先刺探,引綱為援,使冒策立功”;三是李綱當政后,陰與吳敏黨庇蔡京、蔡攸,“其遣攸書,則有密語不敢忘之說”⑤。當然,這些都出自李綱政敵之口,所言不可盡信。宋廷給金人的回書,更明顯是推卸欽宗應負的責任,以李綱、吳敏為替罪羊。但是素來替李綱辯護的朱熹也說:“靖康名流多是蔡京晚年牢籠出來底人才,伯紀亦所不免。”又云:“如吳元忠(敏)、李伯紀(綱)向來亦是蔡京引用,免不得略遮庇,只管吃人議論。”⑥這樣看來,政敵對李綱與蔡攸關系的彈劾并非全出于捏造。清代朱鶴林感慨說:
朱勝非著《秀水閑居錄》詆李綱為蔡京子攸之黨,淵圣受禪,綱與吳敏以詭計取執政,臺諫亦劾綱道君內禪,攸先引綱為援,使冒定策之功。其言宜非可信者。然綱所自撰《靖康傳信錄》云:“吳敏罷相,言者謂內禪事,敏承蔡攸密指,及除門下侍郎,亦攸矯制為之,責授散官安置。余竊嘆曰:‘事已不可為矣。,因入表札奏狀,丐罷。”據此,則綱之黨攸蓋已自吐其實矣。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而其進身乃若此,史豈可曲為之護乎?⑦
蔡氏當國日久,羽翼甚豐,當時士人多出蔡京、王黼之門,李綱由蔡氏引薦,也是極有可能的。朱熹說李綱為蔡京引用,而朱勝非稱李綱是蔡攸黨,《宋史》也說李綱為蔡攸引用。《宋史·蔡攸傳》有這樣一段記載:
時(蔡)翛弟兄亦知事勢日異……密與攸議,稍持正論,故與京異。然皆蓄縮不敢明言,遂引吳敏、李綱、李光、楊時等用之,以挽物情。⑧又,《宋史·張?{傳》與曰:
(蔡)京斂容問計,?{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為第一義爾。”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時薦,于是召時。⑨朱熹也說:
蓋京父子此時要喚許多好人出,已知事變必至,即請張公(?{)叩之。張言:“天下事勢至此,已不可救,只得且收舉幾個賢人出,以為緩急倚仗耳。”⑩
以上材料皆言蔡京父子在宣和間為了稍挽物論,引薦了不少賢能之士。《宋史·蔡攸傳》更明確指出李綱在其列,并由蔡攸薦引。李綱宣和元年(1119)上書論水災,被貶沙陽,第二年復承事郎。六年,除知秀州,七年又除太常少卿。李綱雖因論水災被貶,但已有直聲,蔡攸想通過薦引人才,稍挽物議,李綱是相當適合的人選。此后李綱復官,又被召回京師,與《宋史·蔡攸傳》所言頗為相合。而蔡京宣和二年致仕,宣和六年再起領三省事。張?{與李綱交好,由張觷向蔡京推薦李綱,也極有可能。與李綱同時諸人,或稱李綱由蔡京所引,或說李綱乃蔡攸舉薦。這樣看來,李綱為蔡氏所薦當確有其事。
此外,靖康間李綱為了糾正“眾人所不得而知,書之或失其實”(11)者,編撰《傳信錄》以為自我辯護,敘述在徽宗禪位之際的作為,促成留守之策,保衛京師的功績,出師救援太原的始末,對臣僚彈劾的“冒策立之功”。“假君爵祿以市私恩”,“妄作威福”,“拒抗君命”等所謂的罪狀,作了有力的辯駁。同時,對某些敏感問題也相應的回避,甚至曲筆,其中就包括“卵翼于蔡氏之門,傾心死黨”(12)之論。(13)李綱的不加辯駁等于自吐其實,承認了由蔡氏薦引,與蔡京、蔡攸的親密關系。
二、上書徽宗內禪出于蔡攸授意
《三朝北盟會編》(以下簡稱《會編》)與《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皆云宣和末,徽宗“用給事中直學士院楊子吳敏計,禪位于皇太子”(14)。時吳敏“以給事中伏閤請對,首建內禪之策”(15),士論指敏“為蔡攸死黨”,建請徽宗遜位,乃“蔡攸父子鉤探先旨,計會吳敏為之,冀敏立朝庇其宗禍”(16)。諸史書皆承蔡攸屬意吳敏促成內禪之說,而李綱在此事件中也充當了重要角色。
李綱建炎初罷相,臣僚重提宣和靖康舊事,彈劾李綱“逮上皇將有內禪之意,攸先刺探,引綱為援”(17)。又說:“當時蔡攸出入禁中,刺得密旨,報吳敏、李綱,欲使二人進用,為己肘腋。”(18)朱勝非在《秀水閑居錄》中更添油加醋地說“綱與吳敏以攸詭計取執政”。這類大同小異的記載都指稱李綱、吳敏受蔡攸的指使,請徽宗退位。張邦煒認為這種說法出自李綱與吳敏的政敵之口,很難令人信以為真(19)。可是,對李綱十分推崇的朱熹也說徽宗將謀內禪,親書傳立東宮字付蔡攸,“攸退,屬其客給事中吳敏,敏即約李綱共為之議,遂定淵圣”。又說:“李伯紀,徽廟時因論京城水災被出。后復召用,遂約吳敏勸行內禪事。李恐吳做不得,乃自作文,于袖中入,吳已為之矣。”(20)如此看來,此事當另有玄機。
李綱在《傳信錄》中記載徽宗傳位始末云:
余時為太常少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厚善,夜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杰,與之共守,何以克濟!……”敏曰:“監國可乎?”余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后世惜之。”(21)第二天,即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吳敏進札子,謂徽宗當傳位,并推薦李綱。徽宗令李綱來日候見。次日,李綱尚未入對,內禪之議已決。《宋史·李綱傳》:“疏上,內禪之議乃決。”(22)記載有誤。
據李綱《傳信錄》,是他先向吳敏提出徽宗應傳位,這和朱熹所說吳敏承蔡攸旨,約李綱共議有出入。李綱自言不能盡信,并且存在不少疑點。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徽宗御筆皇太子除開封牧,二十一日宣制,并下罪己求直言詔。是日,李綱應詔上書,論要須治其本原者五,又論陳捍敵十策。但只字未提內禪之事。為何李綱在白天所上的奏疏中不提內禪,到了晚上,卻對吳敏說“事急矣”,當“傳以位號”?
欽宗貶吳敏為崇信軍節度副使、安置涪州時,下詔說蔡攸知徽宗有傳位之意,“乃引給事中吳敏于宣制日,入至玉華閣。又二十三日,引敏連入。”(23)《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云二十二日己未,徽宗召吳敏對于玉華閣,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樞密院蔡攸、童貫,執政張邦昌等人皆在。“或言蔡攸引至玉華閣下者非”(24)。二十一日,吳敏對于玉華閣。是晚,吳敏與李綱定議上言徽宗禪位太子。二十二日,吳敏上札子。《會編》卷五六引臣僚彈劾李綱的章疏云:
吳敏時權直學士院,身在翰林,故其議先達。綱為太常少卿,疏外無由以進。而綱遂懷此札子諸路示士大夫,人無不見之。所論三事,內禪乃其一也。其詞引唐睿宗始立為皇帝,復為皇嗣居東宮事。縉紳見者,莫不駭愕,罪綱失言。由是言之,綱豈知上皇圣意哉?徒得攸言,猶未敢信,且首尾兩端。(25)今《梁溪集》卷四一有《召赴文字庫祗候引對札子》,乃李綱因吳敏二十二日薦,刺臂血書,于二十三日懷此札子待對,引唐明皇避安史之亂,肅宗靈武之立事,乞徽宗假皇太子以位號。與《傳信錄》載李綱對吳敏所言略同。臣僚奏疏中所云李綱引唐睿宗事札子今不見《梁溪集》。臣僚即有彈劾文字,并引其詞,則李綱應作有該札。按時間推斷,當在《召赴文字庫祗候引對札子》之前,約在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當晚,徽宗裝病,命吳敏草詔傳太子位,《會編》卷二五記載始末甚詳(26)。吳敏既在事前上言乞徽宗傳位,又草內禪詔書,可謂居功甚偉。李綱也參與其中,吳敏上書請徽宗遜位,是與李綱商議之后。故李綱在《辭免知樞密院事札子》中自言:“太上皇厭萬幾之煩,欲授圣子,意有未發。臣與少宰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27)
徽宗欲禪位以避金軍,囑蔡攸引合適的人選上言。吳敏承蔡攸意,李綱由蔡氏薦引,受蔡攸器重,又與吳敏相善,并且贊同徽宗禪位,認為此舉有利于抗金大局。(28)蔡攸、吳敏引綱為援,這種可能性是相當大的。聯系此后李綱在圍城中與蔡京、蔡攸“不輟通問”(29),“密語不敢忘”(30),處處為其遮掩罪行。正如朱熹所言,李綱對蔡氏“免不得略遮庇,只管吃人議論”。種種行為證明了李綱與蔡氏的親密關系。吳敏與綱共商大計,翌日遂有吳敏上章及推薦李綱的舉動。由此看來,朱熹所言吳敏、李綱由蔡攸授意,促成內禪應是事實。
三、靖康中陰庇蔡氏的舉動
由于李綱與蔡氏的這種特殊關系,時人詬病李綱在靖康間對蔡氏出于私心,加以庇護。靖康元年(1126)正月,蔡攸隨同徽宗避難逃至丹陽(今屬江蘇),李綱在圍城中,與之通信往來,“其遣攸書,則有密語不敢忘之說”,“至為廋詞云,不敢渝信,又有太師鈞候甚安,此中不輟通問之語。時京在占云館也,其披寫腹心,親密無間,一至于此”(31)。
當時流言稱徽宗將復辟于鎮江,欽宗甚為擔憂。會徽宗批令吳敏、李綱前來,欽宗乃遣李綱往南都(今河南商丘)奉請徽宗還朝。徽宗特別指定吳敏、李綱,一方面是因為兩人建請內禪有功,另一方面恐怕出于身邊蔡攸的攛掇。時吳敏請欽宗令蔡攸勸徽宗北歸以贖罪,李綱受命不久,欽宗就命蔡攸為行宮奉迎副使,則吳敏、李綱乃蔡攸腹心更加明顯。李綱在南都期間與蔡攸接觸頻繁,從當時臣僚的奏章可窺見一二。《會編》卷五五載臣僚上奏說“其(李綱)迎上皇于南都也,與攸耳語移時,蹤跡詭秘,不可具言”。兩人“耳語移時”,談論的內容不得而知,但是李綱回闕不久,欽宗就下詔,以蔡攸力勸徽宗北歸,免受重責,降太中大夫,提舉宮觀,令前去省侍蔡京。所以此后才會有大臣彈劾“綱被詔奉迎上皇,乃請以攸為行宮副使,欲使入朝,都邑震恐。既又以攸有扈從之功,力為營救”,“力欲援攸亦居政府,中外洶洶,莫知所為”(32)。應該說,這些大臣的彈劾并非空穴來風。
由于李綱的功績和聲望,使得史家對他與蔡氏關系多曲筆,諱而不盡言,我們只能從臣僚對李綱的彈劾中作一些推測。如李綱在靖康圍城中,為親征行營使,主管侍衛步軍司,時蔡京“盡室南下,為自全計”(33),臣僚彈劾李綱“遂以守御之卒假京給使。方君父在圍城中,正賴兵眾以為守備,綱乃以資元惡大憝,不忠甚矣”。金人退師后,李綱又薦蔡京入對,臣僚彈劾的章疏云:“蔡京棄去君父,逃于拱州,遣人以奏牘抵綱,使之請對。綱輙敢為京敷奏,京亦恃綱在朝,遽至國門,以俟召命。”(34)由于這些彈劾出自李綱政敵之口,真假難辨。
直到高宗南渡后,張浚在論李綱的奏疏中還說:
(李綱)謂蔡京之罪可略,蔡攸之才可用,交通私書,深計密約,凡蔡氏之門人,雖敗事誤政,力加薦引。(35)張浚出于傾軋李綱的目的,舊事重提,但是李綱“陰與吳敏黨庇蔡氏”(36)確有嫌疑。
當時“吳敏、李綱指燕山之役為黼罪,請誅之,事下開封尹聶山。山遣武吏尋躡,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37)。欽宗在東宮時,就對為鄆王趙楷出謀畫策、陰謀篡奪太子之位的王黼十分厭惡。如果說是王黼曾經動搖東宮,現在又不在徽宗身邊,不致驚動道君”(38),所以欽宗可以無所顧忌。那么“吳敏、李綱指燕山之役為黼罪,請誅之”,但卻請命蔡攸為行宮奉迎副使,則明顯有包庇回護之嫌。宣和中,王黼首贊燕山之役,以童貫為陜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蔡攸為副,出兵與金人夾攻遼國。若要追究燕山失利之罪,蔡攸顯然是難逃其咎的,為何吳敏、李綱單單請誅王黼?曾經動搖東宮,不致“驚動道君”,僅僅靠這些理由是不夠充分的。張邦煒認為出于穩定徽宗情緒與分化徽宗陣營的需要,所以當時出現了“罪同罰異”的混亂現象(39):“故宰相王黼誅死,而蔡京方自拱州請覲,大臣游說,還之賜第”,“謀主宣撫使童貫、王安中、譚稹皆散官安置,而蔡攸乃以大中大夫提舉宮觀任使居住”(40),“其他元惡巨奸,悉已竄逐,獨京父子,尚遲回近甸,未正典刑”(41)。筆者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罪同罰異”現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僅是政治策略這么簡單,一方面牽涉到之前皇位繼承權之爭,另一方面朝臣有意回護也是重要因素。
在有意回護的朝臣中,也包括出于報恩私心的李綱。上文提到,李綱對由蔡氏薦引一事沒有辯解,同樣,對于臣僚“陰庇蔡氏”的彈劾,李綱在《傳信錄》、《時政記》以及紹興年間為了“披露肝膽,控告君父,力賜辯明”(42)而特地撰寫的《辯謗奏狀》中,都沒有加以說明。可見,李綱已經默認自己庇護蔡氏的行為。
四、李綱并非蔡氏同黨
李綱由蔡氏薦引,并且在靖康中有回護蔡京、蔡攸的舉動,招致諸多物議。但從相關歷史資料來看,李綱并沒有趨炎附勢,曲意逢迎蔡氏,更沒有狐假虎威,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
北宋末年,蔡京為鞏固權位,迎合徽宗奢靡心理,大辦花石綱,又興建延福宮、艮岳,“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兩河之民,愁困不聊生”(43)。宣和元年京師大水,李綱在論水災奏章中就大膽揭發蔡京好大喜功,不顧民生疾苦的惡行,指出“比年以來,工役浸多,仰食者眾,歲以侵耗,遂致殫竭”。請求徽宗“凡營繕工役、花石綱運,有可省者,權令減罷”(44)。因此被貶。多年后,徽宗對李綱談及此事,說:“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45)不管此語是徽宗為自己開脫,還是實情,李綱上章必然觸怒了包括蔡京在內的權貴,這也說明李綱并沒有黨附蔡京,奴顏媚上,而是敢于說出事實真相,顯示了他的是非感、正義感和責任感。
據《宋史》所載,蔡氏薦引李綱在宣和中,那么李綱上章論水災是在為蔡氏薦引之前,我們再來看看李綱為蔡氏薦引之后對他們的為政之道又是怎樣一種態度。宣和七年,金人入侵,詔求直言,李綱應詔上封事,指出“比年以來,搬運花石,舳艫相銜;營繕宮室,斧斤不輟;制造器用,務極奢巧;賜予之費,靡有紀極;燕游之娛,倍于曩時”。這些“上累大德,下失群心,蠧耗邦財,斬刈民力”的行為造成了“今日之患”(46),再一次抨擊了蔡京大興工役,導致民不聊生的罪行。
李綱又說:“比年以來,忌諱眾多,人材鮮少;諂諛之說日進,忠鯁之言不聞。”批評徽宗平日“所取謀而聽用者,不過左右近習之臣”。“發號出令,初莫之審;朝令夕改,初不必行。密降旁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束以峻法,而給舍不敢駁”。致使“朝廷為虛設,而政事之出,所以多門也。首尾衡決,先后錯忤,有司疑于趨赴,四方無所適從”(47)。
徽宗時期,御筆手詔頗為盛行。所謂御筆手詔,即不經中書省商議,不由中書舍人起草,不交門下省審覆,由皇帝在宮中決斷,親筆書寫,或由他人代筆,直接交付有關機構執行。御筆之制,蔡京首開先河,請徽宗親書以降,“御筆自此始,違者以大不恭論,繇是權幸爭請御筆,而繳駁之任廢矣”(48)。御筆行事,嚴重破壞了宋代行政決策程序,權幸藉此營私,朝政日益腐敗。李綱所論“密降旁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即是對御筆之制的明確否定,指責了蔡氏等權貴堵塞言路,破壞綱紀的行為。
欽宗登基之后,李綱又上章數徽宗“左右恩寵之臣”罪狀,謂蔡攸“招權怙勢,首為兵謀,以佞幸之姿,據師保之任”(49),請欽宗將其流竄遠方,以正典刑。可見,一直以來李綱非但沒有阿諛逢迎蔡氏,并且對蔡氏禍國殃民的行為進行了強烈的譴責。
李綱出自蔡氏一門是事實。但不等于是蔡氏一黨。陳瓘為諫官,極論蔡氏罪,父子受蔡氏迫害甚重。“瓘平生論(蔡)京、(蔡)卞,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50)。陳瓘與李綱為忘年交,其子弟門人,親屬陳淵、蕭建功等與李綱甚為親厚。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李綱非蔡氏一黨。
通觀北宋末年政壇,人事關系十分復雜微妙。李綱由蔡氏薦舉,并有陰庇蔡氏的舉動,從而受到后人詬病。但不能僅憑這一點,就貶抑否定李綱的品行,實應具體分析李綱的行為表現。李綱在靖康初能夠執政,與蔡氏的薦舉提拔密切相關,但李綱行事與蔡氏截然不同。在蔡氏炙手可熱時,李綱就對蔡氏的諸多妄為,多次加以批評指責。他在靖康間庇護蔡京、蔡攸,當然有顧念舊恩的私心。但與孫覿等人在蔡氏得寵時,極力巴結逢迎,蔡京失勢時,又落井下石的行徑相比,李綱的行為更體現了士人應有的良心。“如蔡京、王黼當國日久,孰不由其擬授”(51)。李綱由蔡氏薦引,不等于是蔡氏同黨。通過上文所舉事例,證明李綱并沒有伙同蔡氏一族禍國殃民。因為由蔡氏薦引這一原因就否定李綱的才行、政聲,完全是不加分析,無視歷史原因的極端作法。
注釋:
①《靖康要錄》,《叢書集成初編》第3882冊,中華書局,1985年,第145頁。
②《三朝北盟會編》(以下簡稱《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13—414頁。
③⑤《會編》,第1434、413頁。
④《大金弔伐錄校補》,中華書局,2001年,第276頁。
⑥《朱子語類》,載《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72、3379頁。
⑦《愚庵小集》卷13,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319冊,1983年,第160頁。
⑧⑨《宋史》,中華書局,1985年,第13732、11696頁。
⑩《朱子語類》,載《朱子全書》,第3374頁。
(11)《李綱全集》,岳麓書社,2004年,第1574頁。
(12)《會編》,第413頁。
(13)參顧宏義《李綱與姚平仲劫寨之戰》,《軍事歷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95頁。
(14)《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中華書局,1988年,第12頁。
(15)《襄陵文集》,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23冊,1983年,第529頁。
(16)(17)(18)(23)《會編》,第309、413、418、404頁。
(19)參見《靖康內訌解析》,《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第73頁。
(20)《朱子語類》,載《朱子全書》,第4072、4086頁。
(21)《李綱全集》,第1575頁。
(22)《宋史》,第11242頁。
(24)《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載《宋史資料萃編》第二輯,臺灣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4425頁。
(25)(26)(29)(30)《會編》,第418、190、417、413頁。
(27)《李綱全集》,第515頁。
(28)參見《李綱全集》卷41《召赴文字庫祗候引對札子》,第502—504頁。
(31)《會編》,第413、417頁。
(32)《會編》,第414、417頁。
(33)(43)《宋史》,第13727、13726頁。
(34)《會編》,第414、417頁。
(35)《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第237頁。
(36)《會編》,第413頁。
(37)《九朝編年備要》,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28冊,1983年,第819頁。
(38)(42)《李綱全集》,第1591、689頁。
(39)參張邦煒《靖康內訌解析》,《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3期,第78頁。
(40)《鴻慶居士集》卷8,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35冊,1983年,第87頁。
(41)《靖康要錄》,《叢書集成初編》第3882冊,中華書局,1985年,第87頁。
(44)(45)(46)(47)(49)《李綱全集》,第492、1592、498、498—500、507頁。
(48)(50)《宋史》,第11123、10964頁。
(51)《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第337頁。
作者簡介:王晴,浙江大學出版社編輯。
李綱(1083—1140),字伯紀,邵武(今屬福建)人,是南宋初第一任宰相、南北宋之交重要的抗金歷史人物。但與生活在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突出、黨爭激烈的這一時期很多重要人物一樣,李綱也有著復雜的人際關系,其與蔡氏(京、攸)的關系就十分微妙,成為當時政敵對其攻擊的炮彈。本文試對此問題作一番考察分析,不當之處,請批評指正。
一、李綱由蔡氏薦引
蔡京、蔡攸歷來被看作是導致靖康之難的罪人。特別是蔡京,在徽宗朝四度任相,排斥異己,汲引同類,“二紀之間,門生故吏,充初天下”①。當時臣僚對李綱與蔡氏關系的彈劾主要集中在三點:一是指稱李綱由蔡氏引用,“平時諂事蔡京、蔡攸”,“卵翼于蔡氏之門,傾心死黨”②,朱勝非在《秀水閑居錄》中說李綱乃“蔡京之子攸黨也”③,宋廷在回答金朝楊天吉等問罪結交余祝的回書中,也稱吳敏、李綱“元乃蔡京、蔡攸之黨”④;二是謂當徽宗內禪之際,李綱受蔡攸指使,上書乞徽宗傳位,“逮上皇(徽宗)將有內禪之意,攸先刺探,引綱為援,使冒策立功”;三是李綱當政后,陰與吳敏黨庇蔡京、蔡攸,“其遣攸書,則有密語不敢忘之說”⑤。當然,這些都出自李綱政敵之口,所言不可盡信。宋廷給金人的回書,更明顯是推卸欽宗應負的責任,以李綱、吳敏為替罪羊。但是素來替李綱辯護的朱熹也說:“靖康名流多是蔡京晚年牢籠出來底人才,伯紀亦所不免。”又云:“如吳元忠(敏)、李伯紀(綱)向來亦是蔡京引用,免不得略遮庇,只管吃人議論。”⑥這樣看來,政敵對李綱與蔡攸關系的彈劾并非全出于捏造。清代朱鶴林感慨說:
朱勝非著《秀水閑居錄》詆李綱為蔡京子攸之黨,淵圣受禪,綱與吳敏以詭計取執政,臺諫亦劾綱道君內禪,攸先引綱為援,使冒定策之功。其言宜非可信者。然綱所自撰《靖康傳信錄》云:“吳敏罷相,言者謂內禪事,敏承蔡攸密指,及除門下侍郎,亦攸矯制為之,責授散官安置。余竊嘆曰:‘事已不可為矣。,因入表札奏狀,丐罷。”據此,則綱之黨攸蓋已自吐其實矣。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而其進身乃若此,史豈可曲為之護乎?⑦
蔡氏當國日久,羽翼甚豐,當時士人多出蔡京、王黼之門,李綱由蔡氏引薦,也是極有可能的。朱熹說李綱為蔡京引用,而朱勝非稱李綱是蔡攸黨,《宋史》也說李綱為蔡攸引用。《宋史·蔡攸傳》有這樣一段記載:
時(蔡)翛弟兄亦知事勢日異……密與攸議,稍持正論,故與京異。然皆蓄縮不敢明言,遂引吳敏、李綱、李光、楊時等用之,以挽物情。⑧又,《宋史·張?{傳》與曰:
(蔡)京斂容問計,?{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為第一義爾。”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時薦,于是召時。⑨朱熹也說:
蓋京父子此時要喚許多好人出,已知事變必至,即請張公(?{)叩之。張言:“天下事勢至此,已不可救,只得且收舉幾個賢人出,以為緩急倚仗耳。”⑩
以上材料皆言蔡京父子在宣和間為了稍挽物論,引薦了不少賢能之士。《宋史·蔡攸傳》更明確指出李綱在其列,并由蔡攸薦引。李綱宣和元年(1119)上書論水災,被貶沙陽,第二年復承事郎。六年,除知秀州,七年又除太常少卿。李綱雖因論水災被貶,但已有直聲,蔡攸想通過薦引人才,稍挽物議,李綱是相當適合的人選。此后李綱復官,又被召回京師,與《宋史·蔡攸傳》所言頗為相合。而蔡京宣和二年致仕,宣和六年再起領三省事。張?{與李綱交好,由張觷向蔡京推薦李綱,也極有可能。與李綱同時諸人,或稱李綱由蔡京所引,或說李綱乃蔡攸舉薦。這樣看來,李綱為蔡氏所薦當確有其事。
此外,靖康間李綱為了糾正“眾人所不得而知,書之或失其實”(11)者,編撰《傳信錄》以為自我辯護,敘述在徽宗禪位之際的作為,促成留守之策,保衛京師的功績,出師救援太原的始末,對臣僚彈劾的“冒策立之功”。“假君爵祿以市私恩”,“妄作威福”,“拒抗君命”等所謂的罪狀,作了有力的辯駁。同時,對某些敏感問題也相應的回避,甚至曲筆,其中就包括“卵翼于蔡氏之門,傾心死黨”(12)之論。(13)李綱的不加辯駁等于自吐其實,承認了由蔡氏薦引,與蔡京、蔡攸的親密關系。
二、上書徽宗內禪出于蔡攸授意
《三朝北盟會編》(以下簡稱《會編》)與《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皆云宣和末,徽宗“用給事中直學士院楊子吳敏計,禪位于皇太子”(14)。時吳敏“以給事中伏閤請對,首建內禪之策”(15),士論指敏“為蔡攸死黨”,建請徽宗遜位,乃“蔡攸父子鉤探先旨,計會吳敏為之,冀敏立朝庇其宗禍”(16)。諸史書皆承蔡攸屬意吳敏促成內禪之說,而李綱在此事件中也充當了重要角色。
李綱建炎初罷相,臣僚重提宣和靖康舊事,彈劾李綱“逮上皇將有內禪之意,攸先刺探,引綱為援”(17)。又說:“當時蔡攸出入禁中,刺得密旨,報吳敏、李綱,欲使二人進用,為己肘腋。”(18)朱勝非在《秀水閑居錄》中更添油加醋地說“綱與吳敏以攸詭計取執政”。這類大同小異的記載都指稱李綱、吳敏受蔡攸的指使,請徽宗退位。張邦煒認為這種說法出自李綱與吳敏的政敵之口,很難令人信以為真(19)。可是,對李綱十分推崇的朱熹也說徽宗將謀內禪,親書傳立東宮字付蔡攸,“攸退,屬其客給事中吳敏,敏即約李綱共為之議,遂定淵圣”。又說:“李伯紀,徽廟時因論京城水災被出。后復召用,遂約吳敏勸行內禪事。李恐吳做不得,乃自作文,于袖中入,吳已為之矣。”(20)如此看來,此事當另有玄機。
李綱在《傳信錄》中記載徽宗傳位始末云:
余時為太常少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厚善,夜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杰,與之共守,何以克濟!……”敏曰:“監國可乎?”余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后世惜之。”(21)第二天,即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吳敏進札子,謂徽宗當傳位,并推薦李綱。徽宗令李綱來日候見。次日,李綱尚未入對,內禪之議已決。《宋史·李綱傳》:“疏上,內禪之議乃決。”(22)記載有誤。
據李綱《傳信錄》,是他先向吳敏提出徽宗應傳位,這和朱熹所說吳敏承蔡攸旨,約李綱共議有出入。李綱自言不能盡信,并且存在不少疑點。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徽宗御筆皇太子除開封牧,二十一日宣制,并下罪己求直言詔。是日,李綱應詔上書,論要須治其本原者五,又論陳捍敵十策。但只字未提內禪之事。為何李綱在白天所上的奏疏中不提內禪,到了晚上,卻對吳敏說“事急矣”,當“傳以位號”?
欽宗貶吳敏為崇信軍節度副使、安置涪州時,下詔說蔡攸知徽宗有傳位之意,“乃引給事中吳敏于宣制日,入至玉華閣。又二十三日,引敏連入。”(23)《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云二十二日己未,徽宗召吳敏對于玉華閣,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樞密院蔡攸、童貫,執政張邦昌等人皆在。“或言蔡攸引至玉華閣下者非”(24)。二十一日,吳敏對于玉華閣。是晚,吳敏與李綱定議上言徽宗禪位太子。二十二日,吳敏上札子。《會編》卷五六引臣僚彈劾李綱的章疏云:
吳敏時權直學士院,身在翰林,故其議先達。綱為太常少卿,疏外無由以進。而綱遂懷此札子諸路示士大夫,人無不見之。所論三事,內禪乃其一也。其詞引唐睿宗始立為皇帝,復為皇嗣居東宮事。縉紳見者,莫不駭愕,罪綱失言。由是言之,綱豈知上皇圣意哉?徒得攸言,猶未敢信,且首尾兩端。(25)今《梁溪集》卷四一有《召赴文字庫祗候引對札子》,乃李綱因吳敏二十二日薦,刺臂血書,于二十三日懷此札子待對,引唐明皇避安史之亂,肅宗靈武之立事,乞徽宗假皇太子以位號。與《傳信錄》載李綱對吳敏所言略同。臣僚奏疏中所云李綱引唐睿宗事札子今不見《梁溪集》。臣僚即有彈劾文字,并引其詞,則李綱應作有該札。按時間推斷,當在《召赴文字庫祗候引對札子》之前,約在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當晚,徽宗裝病,命吳敏草詔傳太子位,《會編》卷二五記載始末甚詳(26)。吳敏既在事前上言乞徽宗傳位,又草內禪詔書,可謂居功甚偉。李綱也參與其中,吳敏上書請徽宗遜位,是與李綱商議之后。故李綱在《辭免知樞密院事札子》中自言:“太上皇厭萬幾之煩,欲授圣子,意有未發。臣與少宰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27)
徽宗欲禪位以避金軍,囑蔡攸引合適的人選上言。吳敏承蔡攸意,李綱由蔡氏薦引,受蔡攸器重,又與吳敏相善,并且贊同徽宗禪位,認為此舉有利于抗金大局。(28)蔡攸、吳敏引綱為援,這種可能性是相當大的。聯系此后李綱在圍城中與蔡京、蔡攸“不輟通問”(29),“密語不敢忘”(30),處處為其遮掩罪行。正如朱熹所言,李綱對蔡氏“免不得略遮庇,只管吃人議論”。種種行為證明了李綱與蔡氏的親密關系。吳敏與綱共商大計,翌日遂有吳敏上章及推薦李綱的舉動。由此看來,朱熹所言吳敏、李綱由蔡攸授意,促成內禪應是事實。
三、靖康中陰庇蔡氏的舉動
由于李綱與蔡氏的這種特殊關系,時人詬病李綱在靖康間對蔡氏出于私心,加以庇護。靖康元年(1126)正月,蔡攸隨同徽宗避難逃至丹陽(今屬江蘇),李綱在圍城中,與之通信往來,“其遣攸書,則有密語不敢忘之說”,“至為廋詞云,不敢渝信,又有太師鈞候甚安,此中不輟通問之語。時京在占云館也,其披寫腹心,親密無間,一至于此”(31)。
當時流言稱徽宗將復辟于鎮江,欽宗甚為擔憂。會徽宗批令吳敏、李綱前來,欽宗乃遣李綱往南都(今河南商丘)奉請徽宗還朝。徽宗特別指定吳敏、李綱,一方面是因為兩人建請內禪有功,另一方面恐怕出于身邊蔡攸的攛掇。時吳敏請欽宗令蔡攸勸徽宗北歸以贖罪,李綱受命不久,欽宗就命蔡攸為行宮奉迎副使,則吳敏、李綱乃蔡攸腹心更加明顯。李綱在南都期間與蔡攸接觸頻繁,從當時臣僚的奏章可窺見一二。《會編》卷五五載臣僚上奏說“其(李綱)迎上皇于南都也,與攸耳語移時,蹤跡詭秘,不可具言”。兩人“耳語移時”,談論的內容不得而知,但是李綱回闕不久,欽宗就下詔,以蔡攸力勸徽宗北歸,免受重責,降太中大夫,提舉宮觀,令前去省侍蔡京。所以此后才會有大臣彈劾“綱被詔奉迎上皇,乃請以攸為行宮副使,欲使入朝,都邑震恐。既又以攸有扈從之功,力為營救”,“力欲援攸亦居政府,中外洶洶,莫知所為”(32)。應該說,這些大臣的彈劾并非空穴來風。
由于李綱的功績和聲望,使得史家對他與蔡氏關系多曲筆,諱而不盡言,我們只能從臣僚對李綱的彈劾中作一些推測。如李綱在靖康圍城中,為親征行營使,主管侍衛步軍司,時蔡京“盡室南下,為自全計”(33),臣僚彈劾李綱“遂以守御之卒假京給使。方君父在圍城中,正賴兵眾以為守備,綱乃以資元惡大憝,不忠甚矣”。金人退師后,李綱又薦蔡京入對,臣僚彈劾的章疏云:“蔡京棄去君父,逃于拱州,遣人以奏牘抵綱,使之請對。綱輙敢為京敷奏,京亦恃綱在朝,遽至國門,以俟召命。”(34)由于這些彈劾出自李綱政敵之口,真假難辨。
直到高宗南渡后,張浚在論李綱的奏疏中還說:
(李綱)謂蔡京之罪可略,蔡攸之才可用,交通私書,深計密約,凡蔡氏之門人,雖敗事誤政,力加薦引。(35)張浚出于傾軋李綱的目的,舊事重提,但是李綱“陰與吳敏黨庇蔡氏”(36)確有嫌疑。
當時“吳敏、李綱指燕山之役為黼罪,請誅之,事下開封尹聶山。山遣武吏尋躡,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37)。欽宗在東宮時,就對為鄆王趙楷出謀畫策、陰謀篡奪太子之位的王黼十分厭惡。如果說是王黼曾經動搖東宮,現在又不在徽宗身邊,不致驚動道君”(38),所以欽宗可以無所顧忌。那么“吳敏、李綱指燕山之役為黼罪,請誅之”,但卻請命蔡攸為行宮奉迎副使,則明顯有包庇回護之嫌。宣和中,王黼首贊燕山之役,以童貫為陜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蔡攸為副,出兵與金人夾攻遼國。若要追究燕山失利之罪,蔡攸顯然是難逃其咎的,為何吳敏、李綱單單請誅王黼?曾經動搖東宮,不致“驚動道君”,僅僅靠這些理由是不夠充分的。張邦煒認為出于穩定徽宗情緒與分化徽宗陣營的需要,所以當時出現了“罪同罰異”的混亂現象(39):“故宰相王黼誅死,而蔡京方自拱州請覲,大臣游說,還之賜第”,“謀主宣撫使童貫、王安中、譚稹皆散官安置,而蔡攸乃以大中大夫提舉宮觀任使居住”(40),“其他元惡巨奸,悉已竄逐,獨京父子,尚遲回近甸,未正典刑”(41)。筆者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罪同罰異”現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僅是政治策略這么簡單,一方面牽涉到之前皇位繼承權之爭,另一方面朝臣有意回護也是重要因素。
在有意回護的朝臣中,也包括出于報恩私心的李綱。上文提到,李綱對由蔡氏薦引一事沒有辯解,同樣,對于臣僚“陰庇蔡氏”的彈劾,李綱在《傳信錄》、《時政記》以及紹興年間為了“披露肝膽,控告君父,力賜辯明”(42)而特地撰寫的《辯謗奏狀》中,都沒有加以說明。可見,李綱已經默認自己庇護蔡氏的行為。
四、李綱并非蔡氏同黨
李綱由蔡氏薦引,并且在靖康中有回護蔡京、蔡攸的舉動,招致諸多物議。但從相關歷史資料來看,李綱并沒有趨炎附勢,曲意逢迎蔡氏,更沒有狐假虎威,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
北宋末年,蔡京為鞏固權位,迎合徽宗奢靡心理,大辦花石綱,又興建延福宮、艮岳,“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兩河之民,愁困不聊生”(43)。宣和元年京師大水,李綱在論水災奏章中就大膽揭發蔡京好大喜功,不顧民生疾苦的惡行,指出“比年以來,工役浸多,仰食者眾,歲以侵耗,遂致殫竭”。請求徽宗“凡營繕工役、花石綱運,有可省者,權令減罷”(44)。因此被貶。多年后,徽宗對李綱談及此事,說:“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45)不管此語是徽宗為自己開脫,還是實情,李綱上章必然觸怒了包括蔡京在內的權貴,這也說明李綱并沒有黨附蔡京,奴顏媚上,而是敢于說出事實真相,顯示了他的是非感、正義感和責任感。
據《宋史》所載,蔡氏薦引李綱在宣和中,那么李綱上章論水災是在為蔡氏薦引之前,我們再來看看李綱為蔡氏薦引之后對他們的為政之道又是怎樣一種態度。宣和七年,金人入侵,詔求直言,李綱應詔上封事,指出“比年以來,搬運花石,舳艫相銜;營繕宮室,斧斤不輟;制造器用,務極奢巧;賜予之費,靡有紀極;燕游之娛,倍于曩時”。這些“上累大德,下失群心,蠧耗邦財,斬刈民力”的行為造成了“今日之患”(46),再一次抨擊了蔡京大興工役,導致民不聊生的罪行。
李綱又說:“比年以來,忌諱眾多,人材鮮少;諂諛之說日進,忠鯁之言不聞。”批評徽宗平日“所取謀而聽用者,不過左右近習之臣”。“發號出令,初莫之審;朝令夕改,初不必行。密降旁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束以峻法,而給舍不敢駁”。致使“朝廷為虛設,而政事之出,所以多門也。首尾衡決,先后錯忤,有司疑于趨赴,四方無所適從”(47)。
徽宗時期,御筆手詔頗為盛行。所謂御筆手詔,即不經中書省商議,不由中書舍人起草,不交門下省審覆,由皇帝在宮中決斷,親筆書寫,或由他人代筆,直接交付有關機構執行。御筆之制,蔡京首開先河,請徽宗親書以降,“御筆自此始,違者以大不恭論,繇是權幸爭請御筆,而繳駁之任廢矣”(48)。御筆行事,嚴重破壞了宋代行政決策程序,權幸藉此營私,朝政日益腐敗。李綱所論“密降旁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即是對御筆之制的明確否定,指責了蔡氏等權貴堵塞言路,破壞綱紀的行為。
欽宗登基之后,李綱又上章數徽宗“左右恩寵之臣”罪狀,謂蔡攸“招權怙勢,首為兵謀,以佞幸之姿,據師保之任”(49),請欽宗將其流竄遠方,以正典刑。可見,一直以來李綱非但沒有阿諛逢迎蔡氏,并且對蔡氏禍國殃民的行為進行了強烈的譴責。
李綱出自蔡氏一門是事實。但不等于是蔡氏一黨。陳瓘為諫官,極論蔡氏罪,父子受蔡氏迫害甚重。“瓘平生論(蔡)京、(蔡)卞,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50)。陳瓘與李綱為忘年交,其子弟門人,親屬陳淵、蕭建功等與李綱甚為親厚。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李綱非蔡氏一黨。
通觀北宋末年政壇,人事關系十分復雜微妙。李綱由蔡氏薦舉,并有陰庇蔡氏的舉動,從而受到后人詬病。但不能僅憑這一點,就貶抑否定李綱的品行,實應具體分析李綱的行為表現。李綱在靖康初能夠執政,與蔡氏的薦舉提拔密切相關,但李綱行事與蔡氏截然不同。在蔡氏炙手可熱時,李綱就對蔡氏的諸多妄為,多次加以批評指責。他在靖康間庇護蔡京、蔡攸,當然有顧念舊恩的私心。但與孫覿等人在蔡氏得寵時,極力巴結逢迎,蔡京失勢時,又落井下石的行徑相比,李綱的行為更體現了士人應有的良心。“如蔡京、王黼當國日久,孰不由其擬授”(51)。李綱由蔡氏薦引,不等于是蔡氏同黨。通過上文所舉事例,證明李綱并沒有伙同蔡氏一族禍國殃民。因為由蔡氏薦引這一原因就否定李綱的才行、政聲,完全是不加分析,無視歷史原因的極端作法。
注釋:
①《靖康要錄》,《叢書集成初編》第3882冊,中華書局,1985年,第145頁。
②《三朝北盟會編》(以下簡稱《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13—414頁。
③⑤《會編》,第1434、413頁。
④《大金弔伐錄校補》,中華書局,2001年,第276頁。
⑥《朱子語類》,載《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72、3379頁。
⑦《愚庵小集》卷13,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319冊,1983年,第160頁。
⑧⑨《宋史》,中華書局,1985年,第13732、11696頁。
⑩《朱子語類》,載《朱子全書》,第3374頁。
(11)《李綱全集》,岳麓書社,2004年,第1574頁。
(12)《會編》,第413頁。
(13)參顧宏義《李綱與姚平仲劫寨之戰》,《軍事歷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95頁。
(14)《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中華書局,1988年,第12頁。
(15)《襄陵文集》,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23冊,1983年,第529頁。
(16)(17)(18)(23)《會編》,第309、413、418、404頁。
(19)參見《靖康內訌解析》,《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第73頁。
(20)《朱子語類》,載《朱子全書》,第4072、4086頁。
(21)《李綱全集》,第1575頁。
(22)《宋史》,第11242頁。
(24)《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載《宋史資料萃編》第二輯,臺灣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4425頁。
(25)(26)(29)(30)《會編》,第418、190、417、413頁。
(27)《李綱全集》,第515頁。
(28)參見《李綱全集》卷41《召赴文字庫祗候引對札子》,第502—504頁。
(31)《會編》,第413、417頁。
(32)《會編》,第414、417頁。
(33)(43)《宋史》,第13727、13726頁。
(34)《會編》,第414、417頁。
(35)《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第237頁。
(36)《會編》,第413頁。
(37)《九朝編年備要》,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28冊,1983年,第819頁。
(38)(42)《李綱全集》,第1591、689頁。
(39)參張邦煒《靖康內訌解析》,《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3期,第78頁。
(40)《鴻慶居士集》卷8,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35冊,1983年,第87頁。
(41)《靖康要錄》,《叢書集成初編》第3882冊,中華書局,1985年,第87頁。
(44)(45)(46)(47)(49)《李綱全集》,第492、1592、498、498—500、507頁。
(48)(50)《宋史》,第11123、10964頁。
(51)《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第337頁。
責任編輯:C009文章來源:《浙江學刊》(2014-03-13)
下一條:沒有了上一條:被出賣的黃樵松將軍
相關信息
精彩展示
沒有記錄!
評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