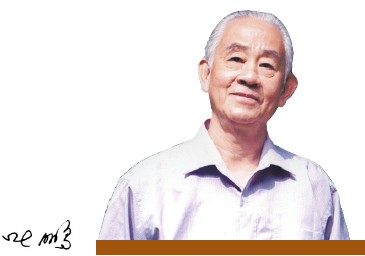-
沒有記錄!
為洛陽代言的司馬光(2)
2013/9/11 10:11:02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司馬光有這個想法的時候,宋英宗還在世。司馬光首先寫出《歷年圖》,將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后周世宗顯德六年之間的歷史編成一個年表,看上去很直觀;接著,他又利用業余時間,編撰了《通志》8卷,敘寫戰國至秦的編年史,這是《資治通鑒》的原名。
英宗看完初稿后,認為很好,鼓勵司馬光繼續編撰。于是司馬光選拔助手繼續編寫,書名暫定為《論次歷代君臣事跡》,這已經有點兒帝王教科書的味道了。英宗死,神宗立,神宗一眼看出此書有“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的作用,可讓君王從中借鑒經驗教訓,于是賜書名《資治通鑒》,并親自動筆寫了一篇序言。
司馬光選定的助手,都是當時一流的學者:他們是司馬康、范祖禹、劉恕、劉攽。其中司馬康是司馬光的兒子,但非其親生,因司馬光無子,過繼了這個兒子。這些助手在東京已收集了4年資料,1071年初夏,他們又跟著司馬光來到洛陽,成立了書局,專門編著《資治通鑒》。
這是一個浩大的編寫工程,司馬光給助手進行了分工,開始時由劉攽整理漢晉南北朝史料,范祖禹整理唐代史料,劉恕整理五代歷史,后來經過調整,讓劉攽整理兩漢歷史,劉恕整理三國至南北朝歷史,范祖禹整理唐代歷史。
編書的所有費用,均由國家財政開支。皇室還把3400多卷典籍送給司馬光,皇家圖書館龍圖閣、天章閣等,也都對司馬光及其助手開放。所以《資治通鑒》的取材十分廣泛,引用書目很多,資料翔實可靠,故古今方家均愛此書。1912年,年方19歲的毛澤東,在湖南省立高中讀書時,從國文教員胡汝霖那里借到此書,深為書中內容所吸引,從此,《資治通鑒》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他,他行軍打仗時也要帶上此書,一生讀了17遍。
二
這本好書,就是在洛陽編寫成的。
許慶西領我來到司馬小學門前,指著一排教學樓說:小時候還能看到祠堂老房舍,祠內有司馬光彩塑像。校園中的一個大殿,幾年前還存在,為了蓋教學樓,拆掉了。老先生感嘆:太可惜了,如果不拆掉,大殿就是標志,殿北就是獨樂園的具體位置,就是編著《資治通鑒》的地方。
我想象不出獨樂園的景致,但在展覽館的墻壁上,看到了讀樂園的復制圖。當時園內有“讀書堂”,收藏圖書5000多冊;有池沼和小島,種竹種花,間有藥圃。園中建筑有“釣魚庵”、“種竹齋”、“弄水軒”、“見山臺”等。
園林風景之外便是“文字風景”。司馬光之所以能代言洛陽,不單單是因為他寫了“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還因他來到洛陽之后,便把時人的目光牽引過來,追隨他的官吏和文人也都在關注洛陽,期待著一部史書在這里問世。
獨樂園竣工后,文人紛紛寫詩祝賀。大才子蘇東坡專門跑來了,寫了《司馬君實獨樂園》:“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杖履,竹色侵盞斝。樽酒樂余春,棋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臥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眾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
蘇東坡名氣大,一首長詩寫下來,就等于推介了獨樂園,也為洛陽作了宣傳。他的弟弟蘇轍,也寫了一首《司馬君實端明獨樂園》,又把司馬光和洛陽城贊美了一番。西京(洛陽)留守宗澤、大學者范祖禹也都寫詩詠贊獨樂園。更有邵雍、張載、程顥、程頤、富弼、呂公著等人因長居洛陽,常來獨樂園吟詩作賦,一時間,花香墨香交融,園林與士林并秀,洛陽城的文氣更濃了。
獨樂園的主人司馬光,自然也要發一番感慨了。他到洛陽后,寫了《初到洛中述懷》一詩:“三十余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角處農桑滿,贏取閭閻鶴發翁。”這首詩總結了他來洛陽之前30多年的為官生涯,表明了自己忠君愛國和激流勇退的胸懷。他還把獨樂園中的讀書堂、釣魚庵、采藥圃、種竹齋、澆花亭、弄水軒、見山臺7處景致,連在一起寫了7首詩。
可是,我徘徊在獨樂園遺址上,反復體味的還是“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這兩句,我猜測他寫下這一詩句時的心情一定特別復雜。作為當代洛陽人,我們也曾如數家珍地向外地人介紹:這里是13朝古都,有105個帝王在此君臨天下;這里文化底蘊深厚,有許多名勝古跡,等等。我們談起洛陽歷史滔滔不絕,我們寫起歷代興衰洋洋灑灑,可我們當中又有誰能用這么簡潔的語言,來概括這座城市呢?所以我在這個簡陋的展覽館前久久流連,顧不上蚊子在臉頰嗡嗡“叮嚀”,從玻璃展柜中拿出司馬光文集,重新閱讀他的這首《過故洛陽城》:“ 煙愁雨嘯奈華生,宮闕簪裾舊帝京。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原以為該詩只有這四句,現在才知道《過故洛陽城》是組詩,共兩首,第一首是:“四合連山繚繞青,三川滉漾素波明。春風不識興亡意,草色年年滿故城。”這才明白司馬光是看了漢魏故城后寫的這首詩,才明白他看歷史是頗有縱深眼光的。
司馬光看洛陽看的是經絡。
而我們看洛陽看的是表征!
三
慣看洛陽經絡的司馬光,當然也能疏通歷史經絡。
《資治通鑒》之前的史書,都是按年紀事,沒有篇目,也不設目錄,閱讀時只能按年份尋找,非常麻煩。司馬光突破了這種舊例,將年表、帝紀、歷法、天象、目錄、舉要、索引集于一體,使讀者查閱時一目了然,開創了編年體史書目錄新體例,把我國的歷史編纂學推到了新的高度,使之與《史記》一起成為史書雙璧,倍受稱贊。1954年冬,毛澤東接見著名史學家吳晗時說:“《資治通鑒》這本書寫得很好,盡管立場觀點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但敘事有法,歷代興衰之亂本末畢具。”
司馬光等人編寫此書的過程非常艱難,“獨樂園”幾成“苦樂園”。
苦就苦在工程浩大,樂就樂在眾人一心。司馬光等人編史時必須先對史料進行考核,追根尋源反復推敲。“編輯部”的房子很矮小,夏天非常悶熱,汗水常常濡濕書稿,司馬光就請人在房中挖了一個大深坑,砌上磚,相當于一個“地下室”,讓大家鉆到里面工作。一日之內,僅司馬光整理謄寫的史料,鋪展于地竟有尺幅之寬一丈之長,每個字都是蠅頭小楷,工工整整從不潦草。他的助手們比他勞作的時間還要長,寫魏晉南北朝部分的劉恕太累了,書未完工就去世了。
來到洛陽的第12個年頭,司馬光65歲。由于過度操勞,他兩鬢霜白,牙齒脫落。他的妻子死后,無錢辦喪事,但他未挪用朝廷劃撥的編書經費,最后賣地葬妻,把喪事辦了。公元1084年,《資治通鑒》終于脫稿,加上在東京編纂的時間,前后共用時19年,書稿堆滿了兩間房子。
《資治通鑒》的完成,使司馬光的威望更高了,“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這年12月的一天,洛陽北風呼嘯,城外霜花滿路,司馬光請人用錦緞裝裱了10個精美的匣子,雇來車馬,載著書稿,往東京送書去了。他的助手劉攽、范祖禹也隨他前往,一路押送,把書稿進獻給宋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