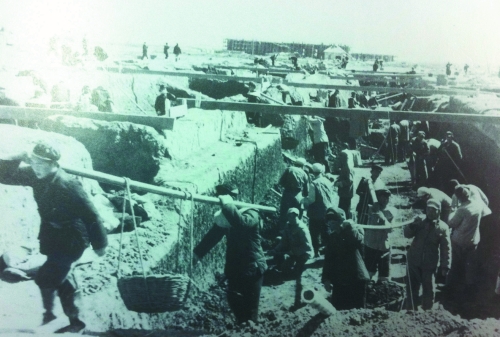-
沒有記錄!
“2013年河南五大考古發現之洛陽衡山北路北魏大墓”系列五 羅馬金幣循著絲綢之路來洛陽
2014/4/24 16:15:10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洛陽衡山北路北魏大墓出土的文物中,有兩件器物讓世人格外感興趣。
一件是陶冊,它看起來就像一本卷起來的雜志,可惜,具體是什么用途無從得知,此前也沒有見過這類東西出土;
另一件就是阿納斯塔修斯(Anastasius)一世金幣,大墓發掘后,流傳最廣的一張照片就是它的正面。
金幣正面雕著東羅馬帝國利奧王朝最后一位皇帝阿納斯塔修斯一世的正面像,兩只眼睛炯炯有神,腦后隨風飄舞的不知是飾帶還是頭發,盔甲和帽子上點綴著珠寶,右手握著一把長矛;背面,是手持十字架的維多利亞女神立像。
金幣通體黃澄澄的,亮得讓人不忍直視。
看到它,我腦海中蹦出的第一個場景,就是第80屆奧斯卡最佳影片《老無所依》里的橋段,殺手安東·奇古爾常常通過讓陌生人猜硬幣的正反面來決定其生死,面對捂著硬幣的奇古爾,加油站老板迷茫而不愿猜,奇古爾隨即說出了經典臺詞:“你知道這枚硬幣是什么年份嗎?1958年,已經過去22年了,這枚硬幣才流浪至此,不是正面就是反面,你猜對了就贏得了一切。”
大墓中的金幣,也恰巧是這次考古發掘中打開謎面的鑰匙,墓葬年代的上限正是基于它的鑄造年代(公元491年至518年)推定。而它本身也是有故事的,難以想象,它在很短的時間內跨越萬公里,從遙遠的歐洲來到中國,它見證了北魏時期的東西方交流,見證了大都市洛陽的輝煌,見證了絲綢之路的奇跡。
它也是欲念的結合體,代表著東羅馬皇室對中國絲綢的渴望,也代表著中國皇室生前的奢侈生活和死后仍不放棄享樂的追求。
最終,在毀墓和盜墓者制造的混亂中,它落入一團泥巴的包圍,卻僥幸留在墓底,平靜地經過漫長的1480年,直到今天,重見天日。
金幣歷時14年行經上萬公里到達洛陽
如今在看守衡山北路北魏大墓的王師傅,對這枚金幣的發現過程記憶猶新,在發掘現場干了多日的活兒,經自己手挖出來的寶貝寥寥,“同村一個以前跑運輸的小伙,來了沒幾天就挖出了個金幣”。
金幣是在墓室的西北角找到的,“一個泥疙瘩,搓搓,出來一個黃顏色的東西”,王師傅回憶,大家都湊過去看,但是金是銅都不知道。只記得,坐鎮發掘現場的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劉斌博士拿到手里,綻開笑容。
多年來,古代東西方的交流一直是熱門課題,不少研究者很關注西方流入中國的貨幣,它們被認為是可貴的物證,其鑄造時代、發現地點都可以提供有價值的線索。盡管從上世紀初以來至2004年前后,國內已經發現了40多枚東羅馬金幣,
但不少都存在問題——不知道其最初的出土地在哪里,進而不能確定其流入中國的年代,另外,相當一部分金幣是制作粗糙、幣面模糊的仿制品。1931年,洛陽就曾發現拜占庭金幣仿制品一枚,發現處不詳,后為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獲得。
“北魏大墓這枚金幣是個例外,不僅不是仿制品,而且品相好,有確鑿無疑的發現地點,說明其至晚在公元532年就已經從歐洲流傳到了洛陽,而阿納斯塔修斯一世金幣的鑄造時間為公元491年至518年。”劉斌說。
也就是說,理論上,這枚金幣最短只用了14年,就從今天的土耳其一帶,行經上萬公里到達洛陽最終進入大墓。考慮到金幣曾被故意剪去邊緣,其應該又被把玩了一些年月,其流入洛陽的速度可能更快。劉斌博士認為,這充分說明了洛陽當時與西方商業交流的繁盛。
那時候,北魏使用的貨幣為孝莊帝元子攸時發行的銅質永安五銖,金幣的價值顯然高得多,又因為這枚金幣的品相格外好,于是它很可能成為北魏皇族的把玩之物,并在死后帶入墓中。
在當時,將罕見而貴重的外國錢幣修邊用來把玩并不是稀罕事,將其作為隨葬品,也不新鮮。我查閱國內出土的東羅馬金幣的記錄,相當一部分金幣不僅是從墓葬中發現的,并且放的位置還很特殊,都位于死者口內或手中。這一特點曾引起一些國內學者對葬俗的考證,有學者統計,在2004年之前發現的42枚東羅馬金幣中,有17枚可以確定是在死者口內或手中。
衡山北路大墓里的金幣,是否也在葬者的口內或手中,因為墓葬被嚴重破壞已無法確知,不過給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間,因為在時間和空間上,與這座墓葬接近的幾例的確是這樣的。比如,上世紀70年代,河北贊皇縣北齊李希宗(公元540年死)墓出土三枚東羅馬金幣,其中兩枚被認為可能含在死者口中或握在手中;70年代末,河北磁縣東魏茹茹公主(高歡的兒媳婦,公元550年死)墓中出土金幣二枚,一為阿納斯塔修斯一世金幣,另一枚為阿納斯塔修斯一世的繼任者查士丁一世(518-527年)時所鑄,發掘簡報稱,金幣可能含在死者口中或握在手中;1981年,洛陽龍門唐定遠將軍安菩墓出土福卡斯(公元602~610年在位)金幣一枚,握于死者右手中。
金幣表達了東羅馬人對中國絲綢的熱切渴望
聽考古學者提到出土的東羅馬金幣有相當一部分是仿制品,心生疑問,那個時候就有人使用假幣了?
還真不是那么回事,紙幣如果造假,沒什么成本,這仿制的金幣,至少也是金子,只不過用料不足。而且,在中國出土的外國古貨幣仿制品,不僅有東羅馬金幣,還有波斯薩珊朝的銀幣。有學者推測,因為東羅馬帝國和波斯的強盛,其錢幣已經成為國際貨幣,而在漫長的絲綢之路中間地帶,中亞的一些商業民族鑄造了一些仿制品,用來流通。
那么衡山北路大墓里這枚金幣因何而來?又是沿著什么線路來到洛陽的呢?
在考古學者眼里,它的出現,只可能跟絲綢貿易有關,并為絲綢之路從洛陽發端再添證據——因為國內已經發現的拜占庭金幣均集中于絲綢之路沿線各省,即新疆、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和河南等。
公元三世紀,曾稱雄于地中海沿岸、版圖橫跨歐亞非三洲的羅馬帝國由盛轉衰,風光不再。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將首都遷往希臘舊城拜占庭,改名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四世紀以后,拜占庭帝國成為歐洲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擔當了歐洲與東方交流的主角。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張緒山在其所著《我國境內發現的拜占庭金幣及其相關問題》文章中認為,當時,中國的絲綢在歐洲貴族中很受歡迎,供不應求,但位于歐亞之間的波斯薩珊王朝(公元224年~651年),以地理優勢牢牢控制了東西方的絲綢貿易。為了得到中國的絲綢,公元298年,羅馬帝國與波斯達成協議,將尼西比(Nisibis)開辟為兩國絲綢貿易口岸。但一個口岸是遠遠不夠的,公元408年至409年,拜占庭帝國為了擴大貿易規模,又與波斯商定,增加一座拜占庭城市和一座波斯城市作為通商口岸,兩大帝國通過這三個通商口岸進行的絲綢貿易持續了大約兩個世紀。
而在東方,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和波斯間的往來較頻繁,《魏書》記載,波斯使臣來中國達數十次之多,給北魏皇帝帶來各種禮品。元恭就曾收過一頭獅子,但他于心不忍把獅子退回去了。
所以,這枚金幣很可能是帶著東羅馬人的熱切渴望,從君士坦丁堡出發,在羅馬與波斯的通商口岸被用來交換絲綢,隨即進入波斯商人的錢袋子,跨越沙漠和崇山峻嶺,來到中亞一帶,抑或再經中亞一些商業民族在絲綢交易中倒手,流入中國境內。
金幣的出土,也使阿納斯塔修斯一世這位異域君主進入我們的視野。他生于約430年,公元491年至518年在位,跨越了孝文帝元宏、宣武帝元恪、孝明帝元詡祖孫三代的在位時間。這是一位政績可與孝文帝相提并論的皇帝,他的登位很特別,他并沒有皇室血統,當過財政大臣和君士坦丁堡宮廷里的御林軍長官,以強干和廉潔著稱,上一任皇帝芝諾死后,他在花甲之齡被元老院推舉為皇帝,還娶了芝諾的孀妻。
當時,在中國人的口中,東羅馬帝國叫做“拂菻”,《魏書·高宗紀》里也叫“普嵐”。阿納斯塔修斯一世和當時的東羅馬貴族一定都知道,東方有一個強大的產絲之國,叫秦尼扎(Tzinitza中國),但他可能沒有時間去操心如何擴大絲綢交易的事,因為他的精力主要用于改革幣值和稅收,跟波斯薩珊王朝打仗,以及抵御周邊落后游牧民族的騷擾。他逝世的時候,給國庫留下了一筆巨大的財富——后繼者們倒是可以拿去消費中國的絲綢。(原標題:“2013年河南五大考古發現之洛陽衡山北路北魏大墓”系列五 羅馬金幣循著絲綢之路來洛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