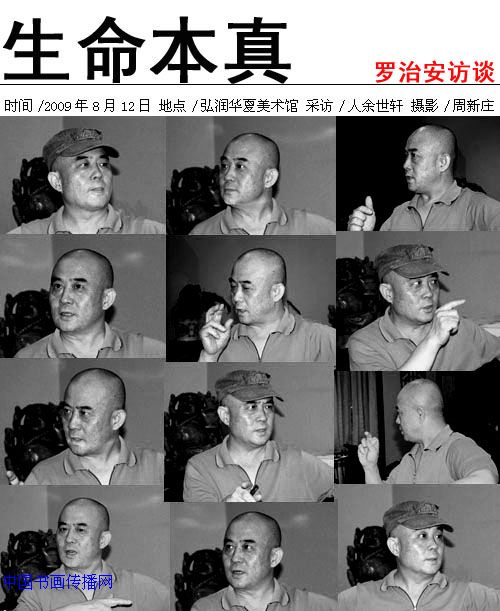-
沒有記錄!
生命本真——羅治安藝術訪談
2013/7/25 12:03:39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時間:2009年8月12日
地點:弘潤華夏美術館
采訪人:余世軒
錄音/攝影:周新莊
余世軒(以下簡稱余):最近是在十一屆美展上看到你的作品,感覺與眾頗不合拍。應該說,很多時候展覽的精神與藝術的本質意義是背道而馳的,先有一個命題在,要求工、求大、求繁、求細……在這個限制中肯定會失去很多原有的東西,你認為呢?
羅治安(以下簡稱羅):你這個問題提出來,現在看,至少有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任何人在自己成長道路當中都要不約而同地接受各種各樣的藝術觀點,理論以及哲學觀、人生觀,每個人雖然是在實踐當中作畫的,但是都會不約而同地被他所了解到的以及所接觸到的那些觀念支配著他對藝術的理解;再一層意思就是,每個人在從小到大的成長道路上,在接受他人的同時,又會各自以為悟得了什么,把從別人那里學來的、理解來的加上自己實踐中體會到的某種東西,容納到一起,形成了各自一個對藝術的一個整體的、決定著他整個藝術實踐過程的錯識或真知灼見。
其實每個人的成長,都不外乎這三種途徑。第一條途徑就是毫無例外的要先受他人影響,這樣就形成了相對樸素的宇宙觀、人生觀、包括各種各樣的認識觀。第二步就是,我在接受他人的同時,又會發出一些疑問,在這樣一個公用的通用的體驗間進行反思、拷問、疑問,經過各種觀念相互類比,以及自己實踐中證明,然后會形成一種帶有個性的、帶有某種專業性的、帶有某種不同于他人的個性化觀點,事實上很多專家學者往往是在這個層面上成立的。但作為真正的認識或真正的智慧,到此是否就到終極了呢?沒有。還有第三種途徑,就是要對以往所知道的一切,來一個全方位的整理和清點——整個世界的誤會就恰恰到這兒是個分水嶺,這之前的任何地方都不是終極。
前兩個層面的區別在于,個別人的認識取代了更多的人。但說到宇宙最根本的性質的話,這兩個層面實際上還是一個意思,就是還沒有究竟。
類似于現在經常看到的各種各樣的展覽,很多展覽的出現,實際上一種就是和那種你知我知大家知的觀念相聯系的產物。還有一些展覽就是,學術啊專業啊就類似這種專業機構所舉辦的這種展覽,從展覽性質上來看的話,似乎和你知我知大家知的那種展覽有種區別似的,但這種展覽也是和這些所謂專家學者的認識是同步的。
如果再往前究竟一下,作為人的生命來看這個現象的時候,在第一個層面,其實這個藝術發生的機制以及里面所有評判的標準,多半是以眼睛為標準而界定的,它的唯一一個尺度要求就是要畫的像不像什么。假如是以鼻子或耳朵為尺度,就不存在這個像不像問題。但問題是,為什么“像”這個東西那么多人堅持著,而歷史的眼光又往往對這個“像”有意無意地給以嘲笑呢?蘇東坡早年就很調侃的說“論畫以形似,見于兒童鄰”,可見這個爭論,真正有智慧者早就看到了,要改變這個現象,就不單單是個藝術的問題了,它其實就是一個對生命要做進一步深刻了解的問題。
余:記得張彥遠也說過,“傳移模寫,畫家之末事”。但繪畫既然作為一種藝術形態產生并且存在了,它首先也應該有個法、有個規則吧?就是說,至少你得在這個規則之內進行。
羅:所謂這個規則和方法,多少人認定,筆有筆法墨有墨法水有水法石有石法甚至勾、皴、點、染各有其法,但它的本質又是什么呢?是法無定法。問題就在于,接受起來“各有其法”很容易,但你把“法無定法”和“各有其法”融和在一起,二者又是不可分割的,這個問題理解起來,就不是一般的認識和智慧所能夠理解的,就牽涉到這個分水嶺啊,很多人的認識也就停留到這里了。大家的認識都知道在眼睛下判斷這是什么,鼻子聞到什么氣味,大家表達,基本上相差也不大。當大家用一個直接的、局部的這么一個尺度評判局部事物的時候,這里面偏差不大,一般用整體觀照人生觀照世界的時候,就出問題了,人的能力多半是在這里產生了差異。
余:所謂見山是山不是山還是山,也許每個人都得經過這三層境界。
羅:這句話是三層意思,含義非常深刻。問題就是,這是清源禪師自己在對人的生命感悟當中,歷經了這么幾個階段,但我們僅僅只是通過耳朵聽到的,然后再通過大腦想象,似乎和某些經驗融通,但這是你親證的嗎?不是。我們三十年前看山也不像山看水也不像水,我們看啥都是朦朦朧朧的。即便剛才談到到以“眼觀”為標準的,其實很多人的眼睛也是迷亂的,并且還要受語言的騷擾。這個語言本身和見到的還是兩碼事,世上不存在任何一個可以用語言很準確的表達的事物,語言文字僅僅是個描述。從本質上說,這些文字語言毫無意義,但這個毫無意義性,好多人都不承認,當然也沒必要要求他非那樣去承認,關鍵問題就是,你得有能力來相信這個東西。
余:文字語言無實義,但繪畫上的這個筆墨,它有沒有實義呢?
羅:記得去年你給我發短信,說“五日一山十日一水”這個觀點成立嗎?如果你認為是這樣的它就成立了。這個話呀,作為語言交流,如果當事者這樣認為,那它就成立了,成立的東西都和你的認識同步的。同樣的話,就剛才說的這個游戲規則,它就這樣認定,它咋會沒有規則呢?但這個規則只是在這一個很狹小的領域里頭存在。
余:那么說到繪畫上的審美,到底什么叫好呢?什么叫究竟呢?
羅:當你用什么樣的“根”來作為尺度衡量的時候,你也是這樣看法或見識,也是固守這個原則的時候,那對你而言它就是好的。剛才談到用“眼根”做標準,不僅中國是這樣,包括西歐,也大量以這個尺度為標準。西歐印象派以前那些作品,毫無疑問它遵循的原則是與“眼根”統一著的。但是后來又有一種變化——這種變化在我看來,實際上是眼睛加上大腦,是以某種想法作為判斷藝術的、一個變形的標準。它們流變的發起點,基本上都是由一個觀念而生出來的東西,似乎就是,你這么一想,你想象的東西和用眼睛看到的東西要發生很多變異啊,而且想象的東西可以把個人的情緒、感覺、欲望,思考等融進去——當想象和欲望構成在一塊的時候會出現一種什么樣的藝術形態?當想象和憤恨構成在一起的時候,又會產生一種什么樣的藝術形態?從這來看,啥叫好呢?不同的構成成分,不同的發生地點,所產生的不同東西,往往又放到一個展覽場地,這個時候你用什么理由什么觀點來證明是綠的對紅的對?這就是因為發生機制不同造成的。
就說中國從古有之的“師造化”,問題你咋師?客觀對象對你直接感應的第一個條件,還是眼睛先觀照這個東西,在可見的范圍內,形成了對這個東西的認識。但你的身體也同樣可以感受到造化中的風啊,雨啊,溫度啊,鼻子對造化中的各種氣味啊,耳朵對造化中各種聲音啊,同樣可以感覺到。但作為繪畫來講,不用其它東西,多半是用眼來“師造化”。從這來看美術史,所謂歷史上多少經典多少國寶,其實有好多都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