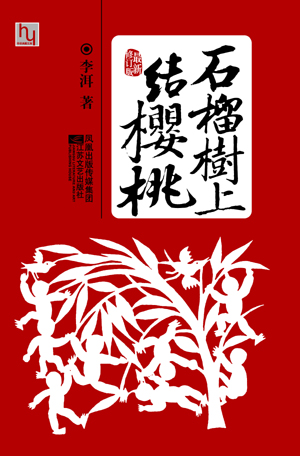-
沒有記錄!
李洱:不知道為什么他們喜歡我?
2013/7/26 9:51:15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訪問中國前,德國總理默克爾選好了送給中國總理溫家寶的禮物:中國作家李洱創作的長篇小說《石榴樹上結櫻桃》的德文版。
10月24日,在北京王府井君悅大酒店,德國駐華大使施明賢把李洱介紹給默克爾。默克爾有個習慣,不管去哪個國家,除了與所在國家領導人展開會談外,她都要與當地參與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見面,以增進對他國的了解。
1小時20分鐘里,默克爾首先談到的是中國農民和農業問題。“我對默克爾博士說,你很難想象,中國的農民坐在田間地頭的時候,他們會談到中美關系、海峽兩岸關系、中東戰爭。他們端個碗蹲在屋前,或者一邊喂豬一邊談論這些問題。有時候他們甚至打打手機,交流一下中程導彈試射誰厲害的問題。他們現在就像老一輩人喜歡談三國、談曹操談劉備一樣,談小布什、薩達姆、陳水扁。農民的生活一方面很現代,另外一方面還比較原始。他們既用現代化的播種機和收割機,也用西漢時期的農具。他們平時也看美國好萊塢的電影。中國鄉村是后現代、現代和前現代的混合。鄉村是中國現實的縮影。”
默克爾還問到有關中國農民們的宗教信仰問題。李洱回答說:“自古以來,在中國人的意識深處,儒道釋三家不分,農民們更是如此。他可以給關公燒香,又同時信奉釋迦牟尼,這在西方看來肯定很奇怪。很多農民也信奉基督教,雖然他可能不知道耶穌兩個字怎么寫怎么念。有時,農民們甚至會供奉一棵老樹,如果他認為樹上住有神靈的話。中國人總是從不同文化當中選擇他需要的那一部分,然后為我所用。當然這說明了中國人對于不同文化的包容和開放心態。這些現象對西方人來講,大概難以理解。”
聊到最后,李洱還說:“很多中國農民對西方的了解,可能要大于西方知識分子對中國的了解。”默克爾聽了以后點頭說, 她認為這是個事實,“西方知識界應該更多了解中國。”
德國熱賣的中國小說
在挑剔的德國圖書市場上,《石榴樹上結櫻桃》的德文版已經賣出了1萬本。
《石榴樹上結櫻桃》的德文版譯者Thekla女士(漢名夏黛麗)在德國慕尼黑講授漢語和中國文學。看到李洱的小說集《饒舌的啞巴》,她非常喜歡。她覺得李洱的小說與她看到的大部分中國小說不同,既有純熟的現代小說技巧,又有著強烈的現實精神。
接到夏黛麗的電話時,李洱正在鄭州大街上的出租車里。李洱向夏黛麗介紹了自己的長篇小說《花腔》。看到《花腔》以后,她非常喜歡,在沒有找到出版社的情況下,愿意自己付版稅給李洱,買下了德文版權。
因為牽涉太多的中國現代歷史和傳統文化知識,《花腔》的翻譯異常艱難。隨后出版的《石榴樹上結櫻桃》,她決定先翻譯這本書。2007年4月,《石榴樹上結櫻桃》在德國DTV出版社出版。DTV出版社又稱口袋書出版社,是德國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
《石榴樹上結櫻桃》在德國出版后,出版社專門為李洱在德國辦了系列朗誦會。德國的奧迪汽車公司還為李洱的德國之行提供5萬歐元的贊助。在慕尼黑和柏林,李洱朗誦中文,一位女演員朗誦德文。德國的記者告訴李洱,這是他們所參加的最好的朗誦會。出版商也沒有想到,朗誦會之后現場的簽名售書就賣了兩百多本。
李洱在柏林換坐地鐵的時候,順便拐進了一家書店。書店門口貼了一張宣傳單,上面有一幅很大的照片,從面相上看是中國人,很熟悉,也很陌生。李洱好奇地走近一看,原來是自己。
回國以后,李洱收到了一個厚厚的信封,里面是一疊報紙,上面都刊登著《石榴樹上結櫻桃》的書評和對他的專訪。“我估計默克爾大概是通過報紙書評知道我的小說的。”《石榴樹上結櫻桃》出版兩個月里,首印的4000冊全部賣完,后來又加印了4次。因為它的暢銷,出版商對他的《花腔》也有了信心。曾經出版余華小說的斯圖加特出版社,以高價買走了《花腔》的版權。
到現在李洱還不清楚,德國讀者為什么喜歡《石榴樹上結櫻桃》。李洱從出版社和翻譯那里了解到,“許多德國人對中國農村的了解,是通過那些來過中國的傳教士寫的書。當他們看到這本書的時候,非常驚訝中國鄉村已經深深卷入全球化進程了,他們想知道這里面到底發生了什么。”《石榴樹上結櫻桃》在西方讀者眼里,是一把打開中國社會大門的鑰匙。2008年3月,企鵝出版社經過調查,最后選出來應該被翻譯到英語世界的中國作家是鐵凝、賈平凹和李洱。
不一樣的鄉土中國
反映中國當下鄉土生活的《石榴樹上結櫻桃》,只是李洱為一部大部頭長篇小說所作的練筆。此前,李洱的小說一直在書寫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困境和生存狀態。
李洱是河南濟源人。他的祖父兄弟4人,有3位到過延安,但后來遭遇各不相同,其中的悲歡離合,一言難盡。李洱的父親是高中語文教師,母親一直在家務農。如父母所愿,李洱和3個弟弟都通過上大學的方式進入了城市,分別成為公務員、大學教師和外科醫生。“坦率地說,小時候在農村,我跟農民們的交往不是非常多。但是很多鄰居、親戚會經常來串門,所以我非常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狀態。我至今仍然和他們保持著交往。”李洱說。
和同為河南作家的劉震云、閻連科、周大新、李佩甫等不同,他們寫鄉土是往非常沉重的地方走,很痛苦,但李洱認為實際上農民是很樂觀的。“他們有一個沉重的痛苦的背景,但他們也有喜悅和快樂,能夠通過反諷從沉重、痛苦中瞬間解脫出來。他們通過戲謔和自我反諷來減輕自己的重負。如果沒有這一面,沉重和痛苦會把他們徹底打垮。”
不久前,《人民文學》雜志約請李洱給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寫一篇短評,李洱在二十多年后頭一次讀了這篇小說。他發現當年陳奐生在縣城旅館里偶然遭遇到的現代生活,比如沙發、席夢思床、電視機,早已經進入到普通農民家庭。但很多的城市讀者對鄉村生活的印象仍然停留在陳奐生生活的那個時代。“中國作家寫鄉土小說是個強項,鄉土中國一直是中國的定義。但以前的中國作家處理鄉土生活的時候,要么把鄉土、農村寫成桃花源、烏托邦式的,比如沈從文《邊城》;要么是階級斗爭式的革命式的,如《紅旗譜》、《金光大道》、《暴風驟雨》、《白鹿原》。它們在很長時間構成了鄉土文學的主要潮流。我們寫了近一百年的鄉土中國,用傳奇的方法寫苦難,其實把鄉土中國符號化了。相對來說,寫‘苦難’是容易的,討好的,而具體寫鄉村生活的‘困難’是困難的。當下這個正在急劇變化、正在痛苦翻身的鄉土中國卻沒有人寫,說得絕對點,我們還看不見一個真正的鄉土中國。”(摘自2008年11月6日《南方周末》 作者:張 英 李邑蘭)【原標題:李洱:不知道為什么他們喜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