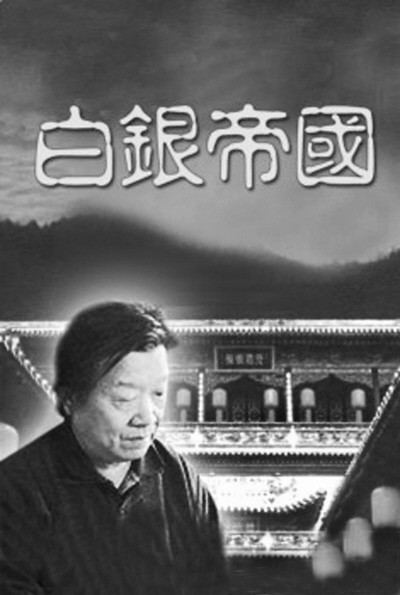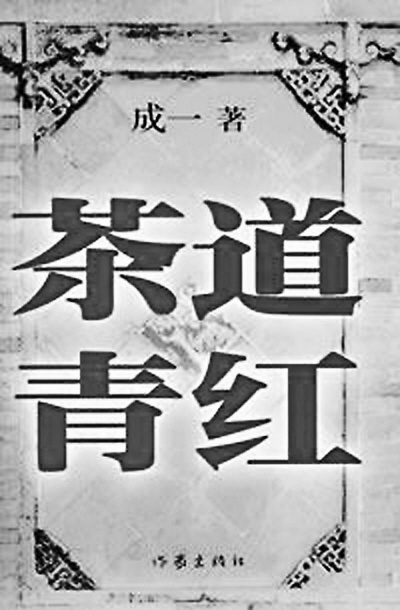“河南墜子滅
本報(bào)記者專訪河南墜子國家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傳承人、第..[詳細(xì)]
宋代理學(xué)家程
程顥(1032年—1085年),字伯淳,原籍河南洛陽,生于..[詳細(xì)]京華時(shí)報(bào)社長(zhǎng)
京華時(shí)報(bào)社長(zhǎng)吳海民接受新浪專訪昨日,京華時(shí)報(bào)社長(zhǎng)、總..[詳細(xì)]
-
沒有記錄!
作家成一:著迷于被歷史遺忘的晉商傳奇
2013/7/26 10:46:20 點(diǎn)擊數(shù): 【字體:大 中 小】
8年前,山西作家成一將《白銀谷》送到老作家馬烽手里時(shí),年過八旬的馬烽調(diào)侃說:“寫了大作了?”當(dāng)時(shí)馬烽身體并不太好,但居然把書看完了,他給成一寫信說:本來想翻翻就撂下,沒想到一看就放不下了。《白銀谷》成為老人一生中看的最后一部長(zhǎng)篇小說。
作家出版社的姜琳回憶起8年前《白銀谷》的出版,一切歷歷在目。厚厚一摞打印稿擺在面前,她想到的第一個(gè)問題是:這么厚的書,誰來買?誰會(huì)看?臨出差的前一天,她隨手抓了一小疊放在包里,準(zhǔn)備打發(fā)旅途的無聊時(shí)光,沒想到,這書稿一看進(jìn)去,就沒再放下手。也幸好沒放下,才有了后來《白銀谷》的入圍茅盾文學(xué)獎(jiǎng),才有了由《白銀谷》改編的同名電視連續(xù)劇和電影《白銀帝國》這兩部巨資投入、明星聚集的影視作品。
寫了30多年小說的成一,年紀(jì)大了,逐漸悟透一個(gè)普通的道理:小說還是要寫給讀者看的。
“被逼”走上文學(xué)之路
成一青少年時(shí)代生活過的太谷縣,是百年前晉商的興盛之地,他祖、父輩兩代也曾在那里經(jīng)商。他讀書的小學(xué)、中學(xué),都是由類似“喬家大院”那樣的富商故居改建的,而自己同學(xué)里也有不少是晉商大戶曹家、孫家的后裔。他說,那時(shí)沒想過要寫小說,但也會(huì)在潛意識(shí)里想這些在大院里生活的人如果活著將是個(gè)什么樣子。
1968年,成一在南開大學(xué)中文系畢業(yè)后,被分配到山西省原平的農(nóng)村接受“再教育”。那時(shí)正是“文革”時(shí)期,而到1978年他寫出第一篇小說,這十年正是中國農(nóng)村改革發(fā)生歷史性巨變的十年。所以,成一早期的很多小說關(guān)注中國農(nóng)民并不意外。他將自己走上寫作道路總結(jié)為是一種“倒逼機(jī)制”:大學(xué)讀中文系,實(shí)在是因?yàn)樘焐?ldquo;色弱”,考理工科受限制,只好讀文科。大學(xué)畢業(yè)又趕上“文革”,什么專業(yè)也沒有了,只有下農(nóng)村。熬到改革開放,有可能考研究生了,學(xué)業(yè)早荒廢,也只好靠底層生活經(jīng)歷來寫作。這是不得已的選擇,當(dāng)然也與從小愛看“閑書”有關(guān)。
成一把自己的創(chuàng)作分為三個(gè)階段,最早是寫農(nóng)村題材,山西的農(nóng)村題材創(chuàng)作比較發(fā)達(dá),有好的傳統(tǒng)。他一上手寫農(nóng)村題材,《頂凌下種》獲得了首屆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jiǎng),成為“文革”之后第一位獲全國獎(jiǎng)的山西作家。發(fā)表于《收獲》雜志的《游戲》是那一時(shí)期的代表作。第二個(gè)階段,從上世紀(jì)80年代中期開始,他辭去《黃河》雜志主編,到祁縣掛職縣委副書記。雖然沒有具體分管某項(xiàng)工作,但是這一職務(wù)為他搜集晉商史料、文獻(xiàn)等提供了很大便利。1993年,他推出了用反偵破筆法揭示了晉商消亡之謎的《真跡》(上海文藝出版社)。這一時(shí)期,文學(xué)本身面臨著調(diào)整,成一也轉(zhuǎn)向?qū)χR(shí)分子、城市生活的關(guān)注,此后又一部《加冕現(xiàn)場(chǎng)》,卻是喜劇中裹著無盡悲涼的苦澀。這兩部成一初涉晉商題材的試水之作以及其他題材的中短篇小說,具有強(qiáng)烈的悲劇性幻滅感的描述,是經(jīng)歷了十年浩劫的中國歷史最直接的情感反射。第三個(gè)階段,以長(zhǎng)篇小說《白銀谷》為標(biāo)志,成一轉(zhuǎn)向晉商題材寫作,他開始建構(gòu)一種實(shí)在的、可以考察的歷史,并嘗試突出作品的可讀性元素。
開始寫小說時(shí),他不愿意被朋友知道,就想了個(gè)筆名:本名王成業(yè),既然在家中排行老大,那就叫成一。漸漸地,他的筆名捂也捂不住了,因?yàn)槌梢幻坎孔髌范紨S地有聲,短篇小說《頂凌下種》獲全國首屆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jiǎng),《綠色山崗》獲1980年《北京文學(xué)》獎(jiǎng)、山西省首屆政府文學(xué)獎(jiǎng)銀獎(jiǎng),短篇小說《遠(yuǎn)天遠(yuǎn)地》獲1979年-1984年《新港》文學(xué)獎(jiǎng),《人樣兒》獲《汾水》文學(xué)獎(jiǎng),《本家主任》獲1981年《山西文學(xué)》作品獎(jiǎng)。寫小說,終于成為他的生活方式,終生職業(yè)。
走進(jìn)晉商的世界
“到了1986年,我產(chǎn)生了轉(zhuǎn)型的想法,因?yàn)橛X得寫農(nóng)村小說也寫不出什么新意,就又把兒時(shí)的晉商情結(jié)翻出來。”成一說,關(guān)于自己的轉(zhuǎn)型,想法非常簡(jiǎn)單,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有讀者。成一那時(shí)四五十歲,是職業(yè)作家,送給親友同學(xué)的作品,他們看了之后,都說內(nèi)容還好,就是“水平高”,看不太懂。“人家也有學(xué)中文的,水平也不差。我發(fā)現(xiàn)自己的作品,評(píng)論家能尋找出很多話題,但是朋友、家人都不看。”年輕的時(shí)候,成一寫自己的純文學(xué),就希望寫出“不一樣”的作品,希望在傳統(tǒng)文學(xué)中找到新意。上了年紀(jì),慢慢轉(zhuǎn)變過來,理解了讀者對(duì)作家的重要性。
之所以選中晉商題材,一方面是這一題材對(duì)今天的讀者來說,本身就具有神秘性,富有傳奇色彩,可以說,晉商的故事本身就如小說般精彩;另一方面,能充分展開故事,人物在事件中沉浮,為作家塑造人物、講述故事提供了很大的空間。還有一點(diǎn),晉商題材吸引成一的,不在它曾富可敵國,而在它從不曾形諸文字。“1986年的時(shí)候,知道晉商的人還很少。由于歷代封建王朝很少過問商業(yè),所以古代官修史料中根本沒有‘商人’這一項(xiàng)。”成一在那段時(shí)間里翻遍了太谷、平遙、祁縣的縣志,但所獲寥寥。
他為搜羅晉商素材,不知翻閱了多少史料,其中獲益的,也不過是有限的幾種。有一本《山西票號(hào)資料匯編》,是“文革”前人民銀行的科研項(xiàng)目,所有涉及到票號(hào)的現(xiàn)存文獻(xiàn)記載,幾乎都編進(jìn)去了。這對(duì)他了解晉商全貌,幫助較大。還有一本上世紀(jì)40年代出版的《山西票莊考略》,是燕京大學(xué)社會(huì)學(xué)教授陳其田所著,作者曾實(shí)地調(diào)查過當(dāng)時(shí)殘存的票號(hào),提供了鮮為人知的一些史實(shí)。而平遙一家老票號(hào)駐北京的掌柜李宏齡,退休后把各碼頭字號(hào)和山西總部的來往信件,整理集結(jié)成一本名為《同舟共濟(jì)》的小冊(cè)子,于中華民國初年石印出來,這本書對(duì)成一獲益最多:使他對(duì)那一時(shí)期的生活陡然增加了感性認(rèn)識(shí)。清朝時(shí)晉商怎么說話,具體稱謂,怎么運(yùn)送銀子……成一說,寫小說和搞學(xué)術(shù)不同,特別難的就是感性認(rèn)識(shí)。書讀百遍,其意自現(xiàn)。真正了解了那段歷史之后,成一的創(chuàng)作基本上駕輕就熟,得心應(yīng)手。
在近90萬字的《白銀谷》中,成一著力加強(qiáng)了故事性、可看性,《白銀谷》的小說和影視劇最大的看點(diǎn),一個(gè)就是展現(xiàn)了晉商200多年的金融傳奇,本身就具有很強(qiáng)的故事性;其次,塑造了幾個(gè)在以前的小說中沒有出現(xiàn)過的人物。對(duì)豪門深藏的善惡恩怨、商家周圍的官場(chǎng)宦海、士林儒業(yè)、武林鏢局、西洋教會(huì)都有著豐滿鮮活、淋漓盡致的描繪。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梁小民在《尋找晉商的足跡》一書中說:“作為山西人,應(yīng)該讓世人知道一個(gè)真實(shí)的晉商。這些年斷斷續(xù)續(xù)讀了一些有關(guān)晉商的資料和著作,也多次去平遙、祁縣、太谷考察、體驗(yàn)。但由于俗事繁忙,始終沒有認(rèn)真研究。山西作家成一先生的小說《白銀谷》激發(fā)了我研究晉商的興趣。讀完這本小說后寫的《探求晉商衰敗之謎》(曾發(fā)表于《讀書》雜志,后收入《我讀》一書中)成為我實(shí)現(xiàn)多年研究晉商夢(mèng)的起點(diǎn)。”
寫完《白銀谷》之后,成一覺得對(duì)晉商表達(dá)差不多了,擔(dān)心再寫難有新意。于是休息了一段時(shí)間,但又覺得積累的茶商素材扔了可惜,便又開始創(chuàng)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