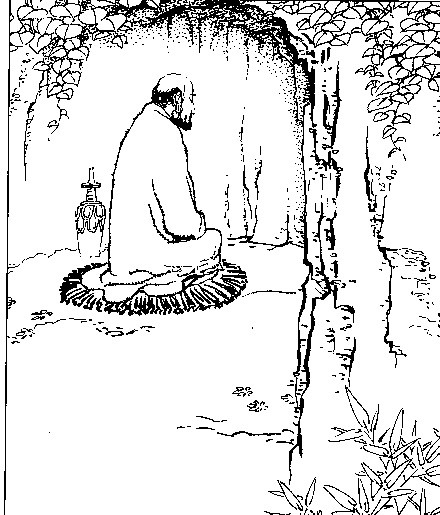-
沒有記錄!
二十九兩紋銀的故事
2013/7/31 15:08:56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王溝村有個王老實,由于一生省吃儉用,家境弄得還算殷實。孩子王浩一天天長大,直到能當家理事,弄啥事總是大大咧咧。老實總嫌兒子不知道仔細(節儉),不防后,就說叨。說說好一會兒,不說,就忘了。嘴上絮出了膙子,兒子媳婦也沒啥變化。有時候憋不住,就說道。說輕了,不濟事;說重了,孩子媳婦就不耐煩。老婆說:“是雞兒都帶倆爪。這輩人不管下輩人的事,你就省點兒心吧。”
王老實覺得委屈:“我是怕他們日后受癥啊。”
老婆說:“你能跟他一輩子?……說說他又不聽——閑著。何勝留口氣暖肚子?老了,別絮絮叨叨惹人不待見。”
王老實覺得老婆說得有理:生就骨頭長就肉,秉性難改。決計不再說他們。可他還是不死心,想來想去,打定主意,得變變法兒。
這天,王老實讓老婆給縫個小布兜。老婆問,縫那弄啥?老實說,攢體己。老婆點著腦袋數落說:“幾百十啦,咋想出這歪點子?——沒你吃哩?沒你花啦?孩子們知道了,看你老臉往哪擱!——我不縫!”
王老實只得說明原委。
兒子媳婦雖然不愛聽老實絮叨,可也孝順。每逢廟會,都唱戲。王浩或者媳婦就拿出些錢,說:“會上有啥好吃的,就買點兒吃吃,甭仔細。”老實一改過去那一套,也不推辭,接了錢就去趕會。到了會上,啥也舍不得買,只給小孫孫買點吃食帶回去。剩下的錢,就裝在那個小布兜里。
閨女來走娘家,給些零花錢,也裝在那個小布兜里。
老婆有了病,孩子們拿出錢來,老實也要從中摳出一些。
隔些時日,老實就來一次以零兌整。
王老實六十八歲,已積攢了二十九兩紋銀。他正摽著勁過三十兩的坎,不料,這時候他病了。
這病來得蹊蹺,剛一上身,就是半身不遂。舌頭硬,嘴也硬,流著哈喇,說話唔哩哇啦,誰也聽不明白。臨終,老實艱難地抬起手,摸著小孫孫的腦袋,淚水像斷了線的珠子,嘴里唔啦的意思是:小孫子啊,恁爹恁娘一輩子不聽說,大手大腳慣了,難有個防后的錢糧,要遇上個天災人禍,恁可咋過哩?……
盡管老實再費心機,可他的話誰也聽不明白。看著一家人迷惑的眼神,老實拍拍胸口,又指指床上,不甘心地咽了氣。
王老實過罷三周年,正趕上光緒三年天下大旱。這個時候,王浩和媳婦才明白老爹絮叨的深意,才想起節儉來。可惜為時已晚,中原大地,赤土千里,餓殍遍野,人吃人哩。王浩夫婦決計陜西逃荒,可缺少盤纏路費,兩口子急得嘴上起了燎泡,活像熱鍋上的螞蟻。悔恨當初沒聽進老爹的話,假如一天省一把,至今也不會這麼熬煎。
這天一大早,王家孫孫王祥一覺醒來,慌慌張張來在上房,見過爹娘,說道:“我夜里夢見俺爺啦!”王浩夫婦一陣凄然。好半天王浩帶著哭腔說:“三年了……老人都走了三年了,還放心不下咱?”
王祥說:“您記不記得俺爺臨咽氣的時候,手拍著心口,指著床上?”
倆人一愣:“記得呀!”
王祥說:“俺爺還是穿著平時穿的衣裳,還是活著那樣子。對我說:‘小孫子呀,你也快成大人啦,懂事了。告訴恁爹娘:不聽老人言,必定受磨難。這一回磨難,可得好好長記性哩。——我怕死后恁受癥,積攢了二十九兩紋銀。本打算攢過三十兩,多攢些哩,就得了病。就放在荊席下,中間的床撐上,在恁奶縫制的小布兜里。切記,好好過日子!”
夫婦倆懵懵懂懂跟著王祥來在堂屋,掀開荊席,見床撐上有一鼓囊囊的小布兜。王浩顫抖著手將布兜打開,果然真是白花花的銀錢!王浩撲騰跪在地上,撲在床前,“爹呀娘呀……”痛哭失聲,媳婦抱著王祥,哽咽著說:“孩兒呀,這就是老人對孩子的心哪!”
有了這些銀錢,王家總算度過了年饉。自此以后,王浩和媳婦真正繼承了王老實“勤儉”的家風。
“人老惜子”的王老實,成了人們流傳中的美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