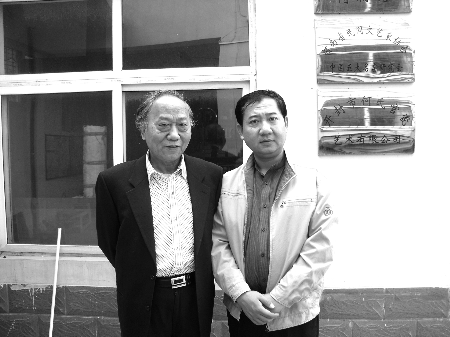-
沒有記錄!
【非遺人物】李力:要留存也要流行
2015/12/17 12:14:14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編者按:青,取之于藍而青于藍。但在非遺領域,許多年輕傳人卻常常感嘆“超越前人很難,創新更難”。如今,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承師命、遵父訓”接過保護和傳承非遺的接力棒。面對傳統,他們懷有敬畏之心;而面對創新,他們卻常常感覺“放不開”。
為此,今年文化部啟動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擬通過培訓幫助提高非遺傳承人群的當代實踐水平和傳承能力。從今年3月始,面對傳統工藝傳承人群的一系列培訓活動在大江南北次第展開。學員中有很多年輕人,他們一起接受學院教授的輔導,聆聽行業前輩的經驗,業余時間互相切磋交流。這一切,為他們打開了思路、指引了方向、樹立了信心。本刊特選取參與過培訓的“80后”進行采訪,讓我們一起來傾聽他們的故事、了解他們的變化。

李力
河南蘭考人,子承父業,開封木版年畫藝人。

李力在給清華大學的學生展示他開發的年畫衍生品
李力:要留存也要流行
自從參加了兩個月前在北京清華大學舉辦的非遺研修班,李力就多了一個外號“老班長”。算下來,李力回到河南開封也有一段時間了,但在微信群里同學們仍愿意這樣稱呼他。他也挺喜歡這個稱呼:“傳承非遺的路不好走,原來我們都覺得自己很孤獨,但在清華我們相識并且成為一個集體,未來還要一起同行。”
李力今年35歲,是開封朱仙鎮木版年畫省級代表性傳承人任鶴林的二兒子,隨了母姓姓李。在開封木版年畫界,任鶴林是個特別有個性的老頭。他16歲考入河南大學藝術系學習版畫,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學生,屬于傳承人中為數較少的學者型傳人。上世紀80年代,在國家倡導恢復和弘揚傳統文化的背景下,任鶴林被調到開封從事傳統木版年畫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后出任開封朱仙鎮木版年畫出版社副社長。1991年,當他對復興傳統木版年畫正充滿干勁兒的時候,由于種種原因,出版社被迫停辦。任鶴林像是被澆了一盆冷水,最終他放棄了“鐵飯碗”,經營起一家小型的印務公司,但木版年畫他并未放下,家里有一點兒閑錢,任鶴林就會用在年畫上。
“父親經常說自己做年畫是工作需要、半路出家,最開始并不喜歡,但是盡管后來沒人要求他再繼續做,他還是守了年畫一輩子。”李力說,在他的記憶里,小時候父母總是會因為要不要堅持做年畫而爭吵,母親對父親的態度也逐漸從對抗、緩和變為不得不妥協。
2002年,李力從河南大學畢業后,便開始幫著父親經營印務公司。李力接下了父親的公司,同時也接下了保護木版年畫的接力棒。盡管當時李力覺得把掙到的錢投在保護木版年畫上看不到任何回報,但他還是支持并跟隨父親花了近10年的時間,將借閱、收集到的300余幅開封木版年畫史料全部復刻并做了數字化。
2006年,他們在開封書店街租下一間200平方米的房子用作木版年畫博物館,免費向公眾展示傳統年畫。在博物館的門上,任鶴林留了自己的電話號碼,只要有人想看年畫,不管多晚,他一定會去開門,不讓人家撲空。李力說,博物館里有一個小倉庫,里面藏著父親一輩子收藏到的一些木版和資料。“父親希望把這些東西都留存下來,好讓后人也能夠看到傳統手工藝人背后的艱辛。”
其實除了把傳統年畫留存下來,在李力心里還有一個給年畫插上翅膀,讓它重新飛翔的夢。為此,他做過許多努力,比如創作新年畫,但收效并不盡如人意。“傳統年畫流傳了千年,無論是設色、構圖,還是人物造型都堪稱經典,事實證明,重新創作的新年畫根本無法超越經典。”李力也嘗試著開發年畫的衍生產品,但總覺得放不開,“在開封年畫界,大家的內心對傳統都有著一種敬畏感,所以有時我的一些想法得不到前輩或同行的響應,自己也不敢貿然往前走。”
參加了清華的研修培訓,讓李力覺得很振奮,老師和同學們的肯定給了他大膽嘗試的信心。在研修期間舉辦的一次展示活動中,一位大學生指著李力帶來的年畫抱枕問:“這個抱枕怎么體現木版年畫?”李力很認真地向他講解了創意的理念和初衷。“若換做是5年前,我肯定會被問得啞口無言。”李力笑稱。
“過去我總是覺得傳統年畫這么好、這么費功夫,人們應該去喜歡它。后來我發現,其實自己的態度可以更主動一點,去做一些能體現年畫元素、點綴人們生活的東西,但最重要的前提是要把東西做精、做好。”李力坦言,通過研修學習,他認識到在非遺創意和設計研發中,創作者的文化素養決定著所做的設計與非遺精髓貼得有多近,在未來的實踐中還需要培養自己對非遺元素抓取和提煉的能力。
- ·朱仙鎮木版年畫進高校系列展演活動啟動
- ·【文化中原】朱仙鎮木版年畫起源與歷史傳承
- ·木版年畫、汴繡等“非遺”項目亮相龍亭公園
- ·朱仙鎮木版年畫
- ·朱仙鎮木版年畫 留住宋韻奇葩 傳承古老文明
- ·【文化中原】民間藝術的活化石——朱仙鎮木版
- ·朱仙鎮木版年畫等亮相第三屆中國非遺博覽會
- ·朱仙鎮木版年畫保護項目獲美國文化保護基金資
- ·【文化中原】豫盛榮傳奇——朱仙鎮木版年畫起
- ·木版年畫極具價值
- ·朱仙鎮木版年畫:門神
- ·朱仙鎮木版年畫
- ·開封朱仙鎮木版年畫傳人—89歲老人郭太運獻藝
- ·朱仙鎮木版年畫:全國首個生態原產地認證的"非
- ·朱仙鎮木版年畫史略
- ·開封朱仙鎮木版年畫成為首個貼上“PEOP”標簽
- ·河南開封木版年畫:紙展神韻
- ·中國最早的木版年畫:朱仙鎮木版年畫
- ·朱仙鎮木版年畫將參加中國“非遺”傳統技藝大
- ·開封朱仙鎮木版年畫的種類
- ·開封朱仙鎮木版年畫簡介
- ·朱仙鎮木版年畫成我國首個獲頒“PEOP”證書非
- ·開封朱仙鎮木版年畫將申報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
- ·開封朱仙鎮木版年畫首個貼上"PEOP"標簽"非遺"
- ·開封市傳承創新做強朱仙鎮木版年畫產業
- ·朱仙鎮木版年畫成我國首個獲頒“PEOP”證書非
- ·開封朱仙鎮木版年畫首獲全國“生態原產地產品
- ·木版年畫吉祥的符號
- ·行走中原感受民間藝術——朱仙鎮木版年畫
- ·朱仙鎮木版年畫傳人任鶴林:免費教學留住物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