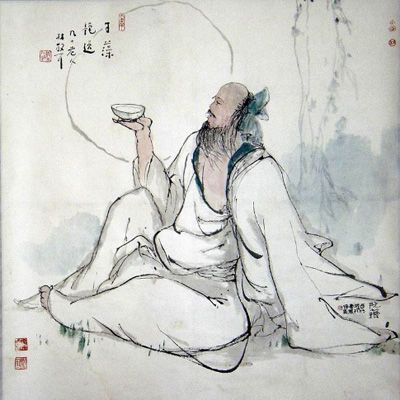精彩推薦
熱點關注
專題推薦
-
沒有記錄!
熱點排行
談談楊業的死因及其歷史教訓
2014/12/4 12:18:08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內容提要:北宋楊家將,在當時以其赫赫戰功,威震華夏;在后代,作為忠勇愛國的英雄,為人民謳歌稱頌,盛傳不衰。但對歷史上楊家將的祖始、大宋開國名將楊業悲慘結局的真象,卻很少有人去細查窮究。
北宋楊家將,在當時以其赫赫戰功,威震華夏;在后代,作為忠勇愛國的英雄,為人民謳歌稱頌,盛傳不衰。但對歷史上楊家將的祖始、大宋開國名將楊業悲慘結局的真象,卻很少有人去細查窮究。即使在新出版的史書上,也僅僅是語焉不詳地淡淡一提:
路上遇遼軍伏擊,敗到陳家谷(朔縣南)口,原來約好在此只援的宋軍撤走了,楊業孤軍力戰,身受數十處創傷,仍然英勇博斗,在狼牙村(今朔縣西狠兒村)被俘,三日不食而死。
這樣一段自相矛盾而又含糊不清的敘述,是偏離了歷史事實而避開了問題的本質和關鍵的。試問,既然是“路上遇遼軍伏擊”而敗,為什么竟“原來約好在此支援”呢?既然是“原來約好”的,為什么在碰巧該支援時,又偏偏“撤走”了呢?是誰要撤走從而導致楊業被俘身亡、整個戰役失敗的呢?這不能不說是些值得研究的問題,因為它不僅涉及如何對待歷史人物的問題,而且包含著一個如何更好地從歷史事件中總結和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的問題。
關于楊業的死因,多年以來,人們都止于對表面現象的了解,錯誤地認為是兵敗身亡。而實際上他也同岳飛一樣,是“為奸臣所迫”,而飲恨長逝的。楊業臨死前曾拊膺大慟:“為奸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楊業所痛斥的“奸臣”,究竟指的是誰呢?人們習慣上都認為指的是潘美,戲曲、演義上也都說是潘美,如對世人影響較大的《楊家府演義》中就有這樣的描述:“卻說仁美(即潘美—引者注,下同)心欲害令公,因其臨去埋伏之言,亦假意與王侁等列陣陳家谷。自寅至午,不得業之消息,使人登托羅臺望之,又無所見。皆以為遼兵敗走,欲爭其功,即一齊離谷口,沿交河南進。行二十里,聞業戰敗,仁美暗喜,引諸軍退回鴉嶺去了。令公與蕭撻懶且戰且走,走至陳家谷,見無一卒,撫胸大慟,罵曰:‘仁美老賊,生陷我也1’大遼韓延壽領兵如蜂集,重重圍定令公父子……”這對歷史上實有其人的另一個宋代名將潘美來說,真是冤哉枉也!誠然,我們決不要求文藝作品完全等同于歷史記載,但要求以歷史為題材的文藝作品,在重大的、關鍵性的問題上,尊重歷史的本來面目,以有助于人們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冤枉潘美,就算是無足輕重吧,但開脫了真正的罪人,掩蓋了一樁具有深遠意義的歷史教訓。
那么,這樁歷史公案的真正罪人究竟是何許人呢?他就是比大將軍潘美更加位高權重、深得宋太宗趙煌信任的監軍王侁里《宋史·楊業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軍北伐,拔寰、朔、云、應等州,“時,契丹****蕭氏,與其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及五押暢隱領眾十余萬,復陷寰州。業謂美等曰:‘今遼兵益盛,不可與戰。朝廷止令取數州之民,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云州之眾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來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褐谷。遣強**千人列谷口,以騎士援于中路,則三州之眾,保萬全矣。’”楊業的這個意見,無疑是完全正確的。但不通戍務、專橫拔扈的王侁,絲毫不考慮楊業意見的正確性,便非常武斷地擅自宣布:“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面對王侁蠻橫而錯誤的命令,楊業出于一個軍事將領的責任心,仍舊據理力爭,極力反對王侁的錯誤決策,說王侁的決策是“不可,此必敗之勢也。”王侁看到楊業一再反對自己的主張,便語帶殺機地質問楊業:“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這個質問,對一個涉世不深,用現在的話說,出身好、歷史清白的年輕人來說,可能是無所謂的。但對楊業那樣一個“北漢降將”說來,真是再沒有比這個質問更富于刺激性、侮辱性和威脅性了。楊業當然比誰都清楚地意識到,這是王侁要抓他的辮子,揭他的老底,清算他的歷史舊帳的危險信號或兇惡予兆。于是楊業便忍受著巨大的屈辱,投入了明知必敗曰戰斗,用“徒令殺傷而功不立”的事實,來表明自己對戰局的正確判斷和自己的“非有他志”。楊業臨行前,曾慷慨悲憤地對潘美表示:“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于敵。”即使到了這個境地,楊業仍然出于愛國軍人對戰局的關注,還是希望能夠把敗局限制在最小范圍,于是提出了最后的建議:“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于此張步兵強**,為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即以步二乓夾擊救之,不然,無遺類矣!潘美確曾按這種籌劃“領摩下兵陣于谷口,但又是王侁“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結果使“屢立戰功,所向克捷,國人號為‘無敵’”的楊業,“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沒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奸臣所追,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楊業這樣一位執干戈,衛社棱,盡力死敵,立節邁倫的宋代名將,最后卻得到那樣一個冤抑慘死的結局,的確是頗足發人深省,從中吸取一些歷史教訓的。試想,倘若當時決定軍事上的行止進退攻守部署的大權不是掌握在不懂軍事,又生“性剛腹”的監軍王侁手中,而是掌握在身經百戰、熟諳韜略的楊業手中,那么,戰爭的結果又會怎樣呢?甚至進一步想,北宋王朝南遷的歷史日程會不會改變?王侁既然長于打小報告,醉心于“一歲中數往來西邊,多奏便宜,上多聽用”,為什么不讓他這類人專搞政治和充當偵探,卻讓他插手具體的戰斗部署,以致具有遠見卓識的軍事將領們的正確判斷和英明決策,遭到無端的干擾與破壞、從而誤人、誤國、誤軍、誤民?
宋太宗對楊業的慘死曾表示“痛惜甚”,下詔追悼,并且將“大將軍潘美降三官,監軍王侁除名,隸金州”但其讓王侁監楊業之軍的本身,就是對楊業政治上的不信任。看來,這種既要利用其業務專長,又不能在政治上予以充分信任的陋習,似乎是古已有之由來頗久的。對楊業之死,王恍固然是直接貴任者,但宋太宗是否能辭其咎呢了實是求是地弄清歷史真象與“為尊者諱”是難于并存的。
楊業之死是由于王侁“以語激楊業”逼著楊業投入必敗的戰斗造成的,而“得非有他志乎”,是王侁對這位有點兒“歷史問題”的軍事將領所祭起的法寶。如果把“有他志”用現代漢語譯出來,就是一個人們并不生琉的成語:“別有用心”。那么,這件法寶是僅僅打中了楊業,還是首先打中了北宋的抗戰安邊事業?這是很可以研究的,因而,“有他志”的究竟是楊業還是祭這件法寶的人自己,也就可以推想了。
北宋楊家將,在當時以其赫赫戰功,威震華夏;在后代,作為忠勇愛國的英雄,為人民謳歌稱頌,盛傳不衰。但對歷史上楊家將的祖始、大宋開國名將楊業悲慘結局的真象,卻很少有人去細查窮究。即使在新出版的史書上,也僅僅是語焉不詳地淡淡一提:
路上遇遼軍伏擊,敗到陳家谷(朔縣南)口,原來約好在此只援的宋軍撤走了,楊業孤軍力戰,身受數十處創傷,仍然英勇博斗,在狼牙村(今朔縣西狠兒村)被俘,三日不食而死。
這樣一段自相矛盾而又含糊不清的敘述,是偏離了歷史事實而避開了問題的本質和關鍵的。試問,既然是“路上遇遼軍伏擊”而敗,為什么竟“原來約好在此支援”呢?既然是“原來約好”的,為什么在碰巧該支援時,又偏偏“撤走”了呢?是誰要撤走從而導致楊業被俘身亡、整個戰役失敗的呢?這不能不說是些值得研究的問題,因為它不僅涉及如何對待歷史人物的問題,而且包含著一個如何更好地從歷史事件中總結和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的問題。
關于楊業的死因,多年以來,人們都止于對表面現象的了解,錯誤地認為是兵敗身亡。而實際上他也同岳飛一樣,是“為奸臣所迫”,而飲恨長逝的。楊業臨死前曾拊膺大慟:“為奸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楊業所痛斥的“奸臣”,究竟指的是誰呢?人們習慣上都認為指的是潘美,戲曲、演義上也都說是潘美,如對世人影響較大的《楊家府演義》中就有這樣的描述:“卻說仁美(即潘美—引者注,下同)心欲害令公,因其臨去埋伏之言,亦假意與王侁等列陣陳家谷。自寅至午,不得業之消息,使人登托羅臺望之,又無所見。皆以為遼兵敗走,欲爭其功,即一齊離谷口,沿交河南進。行二十里,聞業戰敗,仁美暗喜,引諸軍退回鴉嶺去了。令公與蕭撻懶且戰且走,走至陳家谷,見無一卒,撫胸大慟,罵曰:‘仁美老賊,生陷我也1’大遼韓延壽領兵如蜂集,重重圍定令公父子……”這對歷史上實有其人的另一個宋代名將潘美來說,真是冤哉枉也!誠然,我們決不要求文藝作品完全等同于歷史記載,但要求以歷史為題材的文藝作品,在重大的、關鍵性的問題上,尊重歷史的本來面目,以有助于人們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冤枉潘美,就算是無足輕重吧,但開脫了真正的罪人,掩蓋了一樁具有深遠意義的歷史教訓。
那么,這樁歷史公案的真正罪人究竟是何許人呢?他就是比大將軍潘美更加位高權重、深得宋太宗趙煌信任的監軍王侁里《宋史·楊業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軍北伐,拔寰、朔、云、應等州,“時,契丹****蕭氏,與其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及五押暢隱領眾十余萬,復陷寰州。業謂美等曰:‘今遼兵益盛,不可與戰。朝廷止令取數州之民,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云州之眾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來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褐谷。遣強**千人列谷口,以騎士援于中路,則三州之眾,保萬全矣。’”楊業的這個意見,無疑是完全正確的。但不通戍務、專橫拔扈的王侁,絲毫不考慮楊業意見的正確性,便非常武斷地擅自宣布:“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面對王侁蠻橫而錯誤的命令,楊業出于一個軍事將領的責任心,仍舊據理力爭,極力反對王侁的錯誤決策,說王侁的決策是“不可,此必敗之勢也。”王侁看到楊業一再反對自己的主張,便語帶殺機地質問楊業:“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這個質問,對一個涉世不深,用現在的話說,出身好、歷史清白的年輕人來說,可能是無所謂的。但對楊業那樣一個“北漢降將”說來,真是再沒有比這個質問更富于刺激性、侮辱性和威脅性了。楊業當然比誰都清楚地意識到,這是王侁要抓他的辮子,揭他的老底,清算他的歷史舊帳的危險信號或兇惡予兆。于是楊業便忍受著巨大的屈辱,投入了明知必敗曰戰斗,用“徒令殺傷而功不立”的事實,來表明自己對戰局的正確判斷和自己的“非有他志”。楊業臨行前,曾慷慨悲憤地對潘美表示:“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于敵。”即使到了這個境地,楊業仍然出于愛國軍人對戰局的關注,還是希望能夠把敗局限制在最小范圍,于是提出了最后的建議:“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于此張步兵強**,為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即以步二乓夾擊救之,不然,無遺類矣!潘美確曾按這種籌劃“領摩下兵陣于谷口,但又是王侁“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結果使“屢立戰功,所向克捷,國人號為‘無敵’”的楊業,“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沒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奸臣所追,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楊業這樣一位執干戈,衛社棱,盡力死敵,立節邁倫的宋代名將,最后卻得到那樣一個冤抑慘死的結局,的確是頗足發人深省,從中吸取一些歷史教訓的。試想,倘若當時決定軍事上的行止進退攻守部署的大權不是掌握在不懂軍事,又生“性剛腹”的監軍王侁手中,而是掌握在身經百戰、熟諳韜略的楊業手中,那么,戰爭的結果又會怎樣呢?甚至進一步想,北宋王朝南遷的歷史日程會不會改變?王侁既然長于打小報告,醉心于“一歲中數往來西邊,多奏便宜,上多聽用”,為什么不讓他這類人專搞政治和充當偵探,卻讓他插手具體的戰斗部署,以致具有遠見卓識的軍事將領們的正確判斷和英明決策,遭到無端的干擾與破壞、從而誤人、誤國、誤軍、誤民?
宋太宗對楊業的慘死曾表示“痛惜甚”,下詔追悼,并且將“大將軍潘美降三官,監軍王侁除名,隸金州”但其讓王侁監楊業之軍的本身,就是對楊業政治上的不信任。看來,這種既要利用其業務專長,又不能在政治上予以充分信任的陋習,似乎是古已有之由來頗久的。對楊業之死,王恍固然是直接貴任者,但宋太宗是否能辭其咎呢了實是求是地弄清歷史真象與“為尊者諱”是難于并存的。
楊業之死是由于王侁“以語激楊業”逼著楊業投入必敗的戰斗造成的,而“得非有他志乎”,是王侁對這位有點兒“歷史問題”的軍事將領所祭起的法寶。如果把“有他志”用現代漢語譯出來,就是一個人們并不生琉的成語:“別有用心”。那么,這件法寶是僅僅打中了楊業,還是首先打中了北宋的抗戰安邊事業?這是很可以研究的,因而,“有他志”的究竟是楊業還是祭這件法寶的人自己,也就可以推想了。
責任編輯:C009文章來源:楊家將文化研究(2014-06-25)
相關信息
精彩展示
沒有記錄!
評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