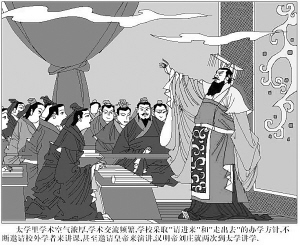-
沒有記錄!
河洛教育史話——秦漢時期
2013/12/2 15:12:27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這也難怪啊,一提到秦代教育,人們便會想到“焚書坑儒”:既然燒了書、坑了儒,還講什么文化?還談什么教育?
其實,說秦代沒有學校是真的;說秦代沒有教育,卻是胡說。秦代教育承前啟后,往前連著夏商周教育,往后開啟了漢代教育;而漢代教育四百年,更是創下了煌煌偉業。尤其是洛陽太學,教育體制之完備,辦學理念之先進,學術空氣之活躍,實為世界古代教育所罕見。
“要寫秦代教育,‘焚書坑儒’是繞不過去的話題!”
提到河洛教育,我市歷史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鄭貞富先說了開頭這句話。
記者提出疑問:歷朝歷代的皇帝,都知儒生是被教育的主體,也是教育的后備力量,難道秦始皇就不懂得這個道理?他為啥要“焚書坑儒”?他不懂得殺戮儒生就是殺戮文化嗎?
1)焚書開始后,大火先從秦都咸陽燃起,接著蔓延到洛陽,千年典籍,灰飛煙滅
鄭貞富認為:秦始皇焚書坑儒,一不是心血來潮,二不是糊涂蠻干,為的是鞏固剛剛建立的中央集權。
一直以來,關于焚書坑儒,流傳著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秦始皇是呂不韋的私生子,這本來已令他苦惱,但那些儒生很“正統”,總是迂腐地去考證“元首”的血緣關系。這使秦始皇很惱怒,就找個理由焚書坑儒,把幾百名知識分子給“坑”了。
第二種說法:秦始皇出宮巡視,晚上住在客店里,見兩個儒生在院中觀星,就躲在大樹下細聽。兩個儒生一高一矮,高的對矮的說:“你看當今天子星在何方?”矮個子說:“瞧,紫微星東移,皇上出京城了。” 秦始皇一聽,怕被人認出來,急忙躲到牡丹花下。可那矮個儒生又說:“不要緊的,皇帝出城,眼下有花王保駕哩!”秦始皇一聽,趕快離開牡丹,躲進客店磨房里。不料兩個儒生同聲驚呼:“怪哉!天子星咋跑到牽牛星座上去了?怎么又進了磨房?!”秦始皇心想,儒生真厲害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還知道我的行蹤,這不利于安全!于是就“焚書坑儒”了。
其實這都是傳說。“焚書坑儒”的真相是:秦始皇一日大宴群臣,仆射(博士長官) 周青臣乘機捧場,稱贊秦始皇:“以前秦國土地不過千里,全靠陛下英明,平定了海內。如今實行郡縣制,各地臣服,天下一統。”嬴政聽了很受用。
博士淳于越反對,說:“周青臣恭維陛下,不是忠臣!商朝和周朝,統領天下一千多年,靠的是分封子弟,作為朝廷的輔翼。現實行郡縣制,不遵循古制了,很不妥。應恢復分封制,把您的子弟分封各地,輔翼朝廷,分治百姓。”
丞相李斯駁斥說:“淳于越迂腐可笑!并不知事物變化之理!現已進入全新的時代,夏、商、周的舊體制,怎值得我們這個時代效法?”他話鋒一轉,矛頭直指儒生:“從前諸侯紛爭,各國用高官厚祿招徠謀士,是那個時代的需要;現天下歸于一統,士人就該順應時代,學習本朝新的法令。可現在的儒生,無事生非,讀死書,認死理,習古非今,惑亂民心。他們開辦私學,標新立說,對現行政策評頭論足,甚至進行誹謗。這極易促成朋黨,需要嚴加禁絕!”
李斯建議:凡不是秦國史書的,一律燒毀!借古諷今者,滅族!
秦始皇采納了李斯的建議——《詩》、《書》及諸子百家的著作:燒掉;兩人以上談論《詩》、《書》者:處死;知情不報者:同罪。于是焚書運動開始,大火先從秦都咸陽燃起,接著蔓延到洛陽,千年典籍,灰飛煙滅。秦始皇還親自圈定460余名儒生,以“妖言”罪處死,活埋于臨潼縣城西20里。
鄭貞富認為:秦始皇焚書坑儒,固然是對教育和文化的一場殺戮,但他為了維護統一大業,也干了些利于后世教育的事情,譬如“書同文”,功績就很大。天下統一之后,各地語言不同,文字迥異,怎么交流呢?就連秦始皇下的詔書,使用的是秦國的文字,各地也不認識啊——所以必須“書同文”。
于是,秦始皇以“小篆” 作為文字形體標準,在全國加以推行。后看到“秦隸”更為人們所接受,就允許民間使用隸書,這為后來書體演變至楷書,奠定了好的基礎。僅此一點,秦朝教育功莫大焉!秦朝雖然短壽,卻是個橋梁,許多方面承前啟后,尤其是博士制教學,直接延續至漢代教育。
2)當時的讀書人,都把來洛陽上太學當成求學時代的美好理想,紛紛前來,絡繹于途
秦亡漢興,西漢教育不述,單說東漢教育。
如今偃師市佃莊鄉,有一個太學村,乃東漢洛陽太學校址。“太學”之稱謂,西周時已經有了。到了西漢,大儒董仲舒建議朝廷立太學,漢武帝采納后,建立了太學院,董仲舒任第一任“院長”。當初規模較小,只有教師5人,學生50人。后慢慢擴大,約有1000名學生。王莽雖然篡了漢,卻特別重視教育,他執政時學生增至3000人。
我市著名學者徐金星先生對東漢太學考證多多,他說:這所大學了不得!學生最多時達3萬余人。在太學任教的“教授”,都是國家級大儒,稱“博士”,職責是“掌教弟子”,以教學為主。但若遇到“國有疑事”,也要“掌承問對”,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討論與修訂,皇帝有時也向他們咨詢疑難問題。他們是朝廷和皇帝的智囊團。
漢光武帝劉秀,重視太學的發展。他上臺后,發出通知,讓那些在西漢末年逃避戰亂的學士迅速歸隊,一時間,四方飽學之士抱負圖書,坐著牛車向京城洛陽趕來。劉秀動用國帑建設太學,使太學校舍“凡所結構達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硬件設施搞得非常棒。當時的大教室“長十丈,廣三丈”,可容納三四百名學生同時聽課。
太學里,學術空氣濃厚,學術交流頻繁,太學生不但有充裕的自學時間,還有充分的自由自選課程。學校采取“請進來”和“走出去”的辦學方針,不斷邀請校外學者來講課,甚至邀請皇帝來演講,漢明帝劉莊就曾兩次到太學講學。這樣一來,太學生們都很關心國家大事,思想活躍,善于論辯,思維敏捷,造就了很多高端人才,像王充、馬融、張衡、鄭玄這樣名垂青史的“高材生”層出不窮。
早在1800多年前,中國就有如此規模宏大和科技領先的太學,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當時的讀書人,都把來洛陽上太學當成求學時代的美好理想,紛紛前來,絡繹于途,其“生源”東至東海,西至西域,連素與大漢結仇的北方匈奴,都派遣子弟來洛陽留學。
那么,太學設置的課程都有哪些呢?
徐金星先生說:主要的課程是儒家經典,但也兼顧天文、歷法、數學各科。但學生終日接觸的主要還是經文,這方面是有實例的:熹平年間,尚有許多儒家經書版本不一,學生們學習起來很不方便,大書法家蔡邕建議朝廷,把統一了的經典寫下來,刻在石碑之上,立在太學門口,成為國家標準教科書,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經》。
3) 東漢的教育,除太學這所國立大學之外,還開辦有“貴胄學校”
在洛陽太學的教育理念中,特別重視學生參與社會實踐和人際交往的能力,學生們在特定時段內可以四處流動,以游學方式走向社會增添閱歷,這自然擴大了士人的交往層面。
東漢的教育,除太學這所國立的大學之外,還開辦有“貴胄學校”。據《洛陽市志》第十二卷記載: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洛陽創辦了“宮邸學”。起因是皇帝外戚子弟,看到太學里的學生成分復雜,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不屑到太學里面就讀。于是漢明帝下令為外戚“四姓小侯”開設了這所“貴胄學校”,招收對象只限光武帝舅家樊氏,明帝舅家郭氏、陰氏,明帝皇后娘娘馬氏四姓子弟。因學校設在南宮,所以又叫“宮邸學”。
宮邸學的設施,比太學更為奢華完善,辦學目的是通過儒家思想教育,使“四姓小侯”子弟懂得君臣之義,使其忠于和維護劉漢王朝。到后來,“宮邸學”招生范圍擴大,凡貴族子弟,不論姓氏,均可入學。學校辦得有聲有色。
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鄧太后又在洛陽創建一所“貴胄學校”。但這所學校規模很小,專為和帝劉肇的弟弟濟北王劉壽、河間王劉開的子弟舉辦,總共只有70名學生。
除了“宮邸學”,還有“鴻都門學”。這是中國最早的國立文藝專科學校,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高等藝術專科學校。學校創立于東漢靈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校址位于洛陽鴻都門,由此得名。
靈帝劉宏喜愛文學藝術,喜好辭賦字畫。宦官集團利用靈帝這一愛好,建立了洛陽鴻都門學。鴻都門學一時興盛,引來不少喜歡文藝的學子,最多時達上千人。鴻都門學里的學子,由于受到靈帝和宦官集團的重視,畢業后走上刺史、太守,尚書、侍中崗位的很多,封侯賜爵的人也不少。
當然,鴻都門學從一開始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對,但朝廷有意呵護這所新型大學,一直到黃巾起義爆發才停辦。這為后人開辦文藝類學校提供了藍本和經驗。
縱觀東漢教育,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由漢代之前各代教育鋪墊的結果:夏、商兩代,主要是“學在官府”的貴族教育,師長多為退職官吏,缺乏青春活力。春秋時期社會變革,對人才的需要量增加,教育沖破了“學在官府”的局面,出現了私人講學。至戰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儒學尤為顯赫。到了秦代,專崇法家,焚書坑儒,對教育進行了摧殘禁錮,但教育只是暫時隱藏起來,蓄勢待發。至漢大興,后勁勃發,尤其是洛陽太學,赫赫煌煌,蔚為大觀,成為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大學。太學到了后來,歷經魏晉隋唐,一直到宋代,還在不斷地培養莘莘學子,他們的經世大用和瑰麗人生,又譜寫出多種版本的歷史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