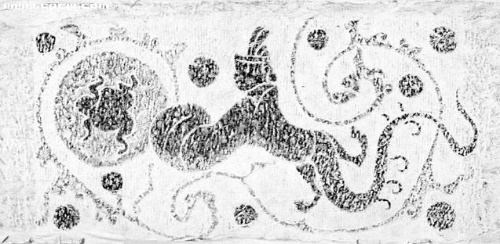-
沒有記錄!
一座內鄉衙,半部官文化
2013/10/22 17:15:43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1)
秦滅六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下設縣。此后兩千多年中,縣始終是封建政權的基層單位,到清代,全國有1591個縣。但清朝滅亡百年之后的今天,長城內外,大江南北,曾經是各地最豪華、最醒目建筑的縣衙竟然難覓蹤影,這,從一個側面見證了百年中國滄海桑田般的巨變。地處伏牛山南麓的內鄉縣,卻把縣衙基本完好地保存了下來。北京的專家們千里迢迢趕到這偏遠小縣,在這里打量著歷史的背影,把這座不再有縣官、不再有衙役的衙門,譽為“神州大地絕無僅有的歷史標本”。“一座內鄉衙,半部官文化”。盛名之下,各色人等紛至沓來,想從這個窗口回望我們陌生而又熟悉的縣衙,品味我們熟悉而又陌生的官文化。
大門:獸頭門環猙獰可怖
冬日的早晨,記者站在了大名鼎鼎的內鄉縣衙門口。縣衙坐北朝南,古色古香,庭院深深,飛檐翹角的房屋層層疊疊,高低錯落。清晨的太陽從東邊照過來,向陽的屋脊上灑滿了溫暖的陽光,而背陰的地方青磚灰瓦地依然幽暗陰冷。明暗冷暖相互映襯,構成一幅很古典的、立體感極強的畫面。
說起縣衙,真不算陌生,古代沒有鄉一級政權機構,縣衙是最接近黎民百姓的政府機關。在《七品芝麻官》、《十五貫》、《卷席筒》、《蘇三起解》等影視戲劇中,見識過不少大老爺升堂問案的場面,所以站在縣衙門口,我有幾分親切感,也有幾分好奇心。
或許是因為我來得太早了,衙門口行人寥寥,喊冤鼓旁邊,工作人員老王靜靜地清掃著地面。喊冤鼓被柵欄圈著,完全成了景觀,我很想敲幾下找找感覺,可踮著腳伸長了胳膊也夠不著。老王過來攔住我:“這鼓不能隨便敲的,過去沒事亂敲要挨板子的。”棄了大鼓,我拿出手機,聯系“衙門”里現如今的“官兒”———縣衙博物館副館長徐新華,熱情的徐館長馬上“擺駕出迎”。老徐是這個博物館最早的倡建者之一,對縣衙潛心研究多年。
衙門衙門,一衙之門先要看個仔細。縣衙大門面闊三間,中間是明間過道,黑漆大門上,一個猙獰的獸頭門環格外引人注目,據說各級衙門的大門上都有這樣一個門環,就連故宮龍頭朱漆大門上的獸頭門環也同樣猙獰可怖。獸頭不美也不祥和,古代大大小小的官兒為什么格外偏愛這“動物兇猛”?徐新華說,實際上,衙門的“衙”通牙齒的“牙”,原意是指帶有獠牙的門。在尚武的唐朝,衙門和牙門通用,而到了斯文的宋朝,人們逐漸不知道牙門為何物了,但門上猙獰的獸頭卻保留了下來。在古代,衙門是官府和權勢的象征,猙獰的獸頭體現了政權的強制性特征,說白了,就是用這個嚇唬老百姓,制造森嚴壓抑的氣氛,讓老百姓望而生畏。門房的東間前置喊冤鼓,供百姓擊鼓鳴冤之用;西間前有兩通石碑,分別刻著“誣告加三等”、“越訴笞五十”字樣。越訴就是越級告狀的意思,在古代這是影響縣官政績的事兒,所以大老爺在衙門口立下石碑,明文規定越訴要打50下屁股。
古代有俗話說:“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別進來。”當時人們在走進衙門時總是很猶豫,這里是人們不得不依靠的國家機構,可里面又隱藏著說不清道不明的黑暗和齷齪。別的不說,就是打板子時這板子的輕重差別可就大了。有記載說,在內鄉縣衙大堂上,時常有人被板子活活打死。過去人說“天下衙門深似海”,不光說的是衙門規模大房子多,更是說里面人精多,門道多,竅門多。
現如今的內鄉縣衙也是“無錢別進來”。因為這是全國保存最完好的縣衙,又是全國第一家衙門博物館,進這個門要30元錢的門票。即便如此,這里還是人流不斷,除去手持各種“條子”免費的,博物館每年的門票收入還有一二百萬元,在內鄉這樣的山區縣,這可不是個小數目。
儀門:禮儀之門規矩繁多
在內鄉縣衙走了一圈,最讓我感到別扭的,是儀門;最讓我慶幸沒生在古代的,是大堂。
在縣衙轉悠,明顯感覺到門多,過一道門又一道門,讓人感嘆庭院深深深幾許。儀門是進了衙門后的第二道正門,這個建筑沒別的用途,唯一的用途就是在大門和大堂之間多設一道門。
儀門,取“有儀可象”之義,是一道禮儀之門。門修得很寬敞,但好好的門平時緊閉著,不讓人走。從此經過要走兩邊低矮的便門,并且兩邊的便門很不相同。西側的便門稱“鬼門”,也叫“死門”。“死門”平時關閉不開,只有在處決死刑犯前,才打開這個門,把死刑犯從這個門里拉出去行刑。因此舊時處決犯人也叫“出西門”,有上西天之意。東側的便門稱“人門”,也叫“生門”,這才是供人們日常出入的。在一年中,寬敞的儀門一般會開幾次,比如逢著新官到任,或迎接同級、上級官員來訪,縣官就會下令大開儀門,自己也整冠出迎至儀門之外,大門以里,賓主從儀門而入(賓走西階,主走東階)。大堂如有重大慶典、禮儀活動或審理重大案件時也大開儀門,讓百姓人等從中門而入,到大堂前參加慶典或觀看縣官審案。
聽著介紹,我不禁感嘆古人的規矩太多。縣衙博物館專門研究官衙文化的劉鵬九先生笑了:“細說起來規矩才多呢!你們年輕點的才不耐煩呢!”劉先生說,下級官員初次拜見上級官員要身著公服,從儀門東側的便門進來,到長官面前要先將寫有自己職銜、履歷的名柬交上去,口稱“卑職給大人請安”,行半跪禮。人家請就坐,還要謝座。就坐后,側身面向“領導”,取半坐姿勢,回答領導第一句話要起立作答,等領導示意坐下再就坐。一般談話要結束的時候,侍者會端茶過來,但這茶千萬不能喝,這是領導表示“你該走了”,即所謂“端茶送客”,這時不立馬告退的都是傻子。俗話說“官大一級壓死人”,在清代的官場,這句話可真是一點不夸張。
大堂:刑具多多氣氛森嚴
進了縣衙大門,百米長的青石甬道穿過儀門直通大堂。大堂、二堂、三堂是縣衙中軸線上的三大主體建筑,都建在高高的臺基上,顯得格外高大巍峨。其中大堂是整個衙門的中心建筑,最為壯觀。大堂面闊五間,高11米多,建筑面積248平方米。大堂上方懸掛著“內鄉縣正堂”行楷金字匾額,堂前粗大的黑漆廊柱上有抱柱金聯,上聯是“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下聯是“負民即負國何忍負之”。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知縣掌握著一縣的行政、立法、司法大權,這幅清代名聯是大權在握、缺少制約的官員對自己的告誡。
大堂是知縣發布政令、舉行重大典禮、公開審理案件的地方,也是我們最為熟悉、在電視上看得最多的地方。內鄉縣衙大堂中央有一暖閣,是為知縣審案設的公堂,內有三尺公案,上面放著驚堂木、文房四寶及紅綠頭案簽。紅頭簽為刑簽,是下令動刑的;綠頭簽為捕簽,是下令捕人的。當這簽擲地有聲的時候,便意味著一項重大案件正在審理的過程之中,馬上就有人要皮開肉綻或被捉拿歸案了。看看內鄉縣衙大堂的架勢,或許能讓我們感覺到古代官衙的嚴刑峻法。
暖閣正面屏風上繪著海水朝日圖,寓意是為官者要清似海水,明如日月。再上頭,照例有“明鏡高懸”的匾。
暖閣前地坪上保留有兩塊青石板,東為原告石,西為被告石。兩塊石板上現在留有四個明顯的跪坑,那是古人拿膝蓋磨出來的。暖閣外兩側分別擺放著堂鼓、儀仗及刑具。東側的刑具架上,擺著10多根黑紅各半的水火棍,據說黑色象征水,紅色象征火,寓意是罪犯的行為和國家的法律猶如水火互不相容。細看起來這些刑具很有講究,有比較細的竹板,有粗大的木板,木板又有寬的、窄的和四棱子的,打起人來自然輕重大不相同。
據介紹,古代司法的主導思想是主張息訟,不主張打官司,所以有“入門三分罪”的說法,原告、被告都要長跪在堅硬的石板上,都要吃板子。受刑時男女不同,打男人是放翻在厚實的椿木凳上打屁股(據說打屁股是大唐天子李世民發明的,唐以前刑罰沒固定部位,常打在腰背上,把人當場打死。李世民看到一張針灸圖,發現腰背上穴位很多,而屁股上穴位很少,于是開恩下了圣旨,從此公堂上打屁股就成了定例);打女子則打在手掌上。
相比起來,西側的刑具更可怕,墻根擱著夾棍,墻上掛著拶子。夾棍由三根木頭做成,俗稱“三木之刑”,是在審理人命案或者其他重案時,對證據確鑿而拒不認罪的男性人犯使用的。據說上了夾棍疼痛難忍,手上加點勁就會夾斷腿骨。拶子是為女犯人準備的,是專夾女人手指的刑具,也能讓人痛徹骨髓。古代男人勞動主要靠腿,女人勞動主要靠手,所以夾棍和拶子這樣的刑具破壞的都是人的勞動能力。即便是在殘酷的古代,使用這樣的刑具也必須稟告上級,驗明烙印,并且限定在一次案件中對同一個犯人使用不得超過兩次,否則就按酷刑逼供論處。
審案時,堂役擊堂鼓三聲,三班衙役兩廂伺立,齊聲高叫升堂,知縣身著官服從暖閣東門進來,坐上大堂,然后原告被告被帶上來,分別在大堂的原告石和被告石上跪下。退堂時也擊鼓三聲,叫做退堂鼓。退堂鼓成為日常生活用語,可見衙門文化的影響。
明清兩代,知縣很講究大堂辦事,為的是能“日與百姓相見”,加強他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和政治影響。對某些“不逞之徒”要“坐大堂對眾杖之”,甚至“示以不測之威”,以懲一儆百,教育多數百姓,由此可見大堂的重要作用。
大堂后,還有二堂三堂等主體建筑。二堂是知縣預審、初審和調處一般案件的地方。知縣在此恩威并施,對當事人進行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倫理思想教育,通過調解,征得雙方同意,達到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目的。
三堂是知縣日常辦公、接待上級官員和商議政事的地方,一些涉及機密和不宜公開的隱私案件也在此審理。三堂的內部格局與大堂、二堂迥然不同,東邊兩間為接待室,西邊兩間為知縣的起居室和更衣室。三堂左右兩邊是東西花廳院,是知縣及其眷屬居住的地方。后面為縣衙的后花園,供知縣賞心悅目、陶冶性情。
(2)
“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別進來。”全國各地的衙門蕩然無存了,可對于古代衙門黑暗的這種嘲諷,我們至今耳熟能詳。封建時代的吏治時好時壞,但歷朝歷代的貪官污吏都不在少數。中國人堅信“有理走遍天下”,可就是到了衙門口的時候信心就不足了,古代大大小小的衙門到底怎么了?仔細看看內鄉縣衙或許能明白點什么。
“邑令催科無去處,班頭衙役俱逃亡。”著名史學家史樹青先生這兩句詩我早就看過,原來覺得很是風趣,但到了他所吟詠的地方,才感覺到一種詠古之幽情。百年前,按照古代的作息時間,這個時候衙門里上上下下都該忙碌起來了,可現在眼前既沒有挎腰刀的捕快、扛水火棍的衙役來回穿梭,也沒有留長辮穿長袍表情忐忑的圍觀百姓,更沒有喊冤鼓驟然敲響的悲憤和板子落下時的凄厲呼號……歷史已經遠去,往日不會重現,舊日的喧嘩已經被現如今的寧靜所代替。衙門不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縣官和衙役“俱逃亡”,空空的院落成了一個供人觀賞的“標本”。
三班吃陋規 六房收黑錢
內鄉縣衙長方形的大院子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四合院,這些四合院各自功能不同。儀門東側的一個四合院,是皂、壯、快三班衙役值班的地方。皂班值堂役,負責站堂;壯班做力差,負責內勤;快班做緝捕,負責抓人。這些人統稱為衙役,是古代最基層的“執法人員”,跟老百姓接觸最多,很大程度上代表著衙門的“形象”。
進了儀門,兩側分列著吏、戶、禮、兵、刑、工六房。這六房與中央政府的六部相對應,內鄉縣衙博物館副館長徐新華通俗地解釋說,吏房相當于現在的組織部,戶房相當于現在的財政局加民政局,禮房相當于教育局,兵房則是武裝部,刑房相當于公安局加司法局,工房則是城建局和水利局。每房有書吏2~3人。
別小看了三班六房,《水滸傳》中的及時雨宋江、打虎英雄武松、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橫等,在上梁山前都是在縣衙的三班六房上班。
從現存的建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古代一個縣的行政機構基本都集中在了縣衙,全部行政管理人員大約有100多人。依清代官制,縣令為正七品,縣令以下,有八品、九品的縣丞、主簿、巡檢、教諭以及一些不入流的官。但根據制度,全縣“吃皇糧”的朝廷命官只有十來個人,其他職能部門如三班、六房等吏、役都無品級,不在官員之列。
六房的書吏大多讀過書。他們大都是科場失意后,通過招募考試成為吏員的。書吏們是衙門的文職辦事員,沒有俸祿,合法的收入是很少的紙筆費、抄寫費和飯食費。知縣是一縣之尊,還有縣丞和主簿輔佐,但他們都是外地人,對本地情況不熟悉,也不可能勝任衙門內的全部事務。在衙門中真正辦事的是這些書吏,他們承攬了衙門的全部事務,因此獲得了權力,所以有“清朝與胥吏共天下”的說法。
衙役們享受國家“工食銀”,每年六兩或二三兩不等。但他們社會地位低下,《大清律例》把他們貶為賤籍,其子孫三代不得入仕做官。很多家族規定嚴禁其子孫充當衙役。
衙門里有大批這種手中握有權力而心理很不平衡的人,于是“吃陋規、收黑錢”成為衙門公開的秘密。所謂陋規,是歷來相沿的不成文規矩,不合理不合法,但大家習以為常。按照清朝有關規定,六房書吏任職不得超過五年,但實際上很多書吏世代相傳,他們對衙門內情況極為熟悉,營私舞弊很有一套,處處變著法盤剝百姓。對于進衙門打官司的百姓,衙役和書吏們用各種招數敲詐勒索。高高在上的縣官對此也很清楚,但卻無法根治,“任憑官清如水,無奈吏滑似油”,說的就是衙門的這種弊端。
“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別進來。”積弊多多的衙門如同陷阱,老百姓一旦進來,就很難全身而退。有一首《息訟歌》曾廣為流傳,專說衙門中人如何“索錢有方”:
“聽人教唆到衙前,告也要錢,訴也要錢。差人奉票有逢簽,鎖也要錢,開也要錢。地鄰干證車馬連,茶也要錢,酒也要錢。三班丁書最難言,審也要錢,和也要錢。自古官廉吏不廉,打也要錢,抄也要錢。”
千里去做官 為的銀子錢
《十五貫》中的胡來胡知縣有段很精彩的唱詞:“兩個老婆來告狀,我一人罰她倆雞蛋;兩個鐵匠來告狀,我一人罰他兩張鐮。”《竇娥冤》中,楚州太守出場白就是:“我做官的勝別人,告狀來的要金銀,若是上司來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門。”開庭審問時,太守見張驢兒跪下,竟然也急忙下跪。下屬說:“他是告狀的,怎生跪他?”太守答:“你不知道,但來告狀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戲劇是夸張的,這樣不要一點體面的貪官兒可能并不多見。衙門里也出了不少好官,戲劇中“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的唐成不用說,放浪形骸的鄭板橋當了縣官,曾做詩說:“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其關心民間疾苦之情殷殷。當然,極好和極壞的官兒都是少數。封建時代官場廣為流傳的“千里去做官,為的銀子錢”(另一個版本是“千里去做官,為的吃和穿”),恐怕道出了大部分官員真實的心態。
古代實行嚴格的回避制度,做官必須到離自己家鄉500里以外的地方去,所以元明清三代內鄉的幾百個縣官沒有一個是本地人。離開家鄉幾百里甚至千里之遙去做官,目的是謀得終身吃穿,所以才會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說法。有人算過一筆賬,知府每年的俸祿為105兩,養廉銀每年4000多兩,三年的合法收入是12300多兩,一位清正廉潔的知府,怎么會掙到10萬兩雪花銀呢?原來還有名目繁多的“敬”,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過年過節、婚喪嫁娶還有拜禮、賀禮等,算下來每年可得數萬兩,這樣一個任期下來,十萬銀子就到手了。當時人們對官吏廉與不廉有這樣的區分標準:“廉者有所擇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羅致,結拜師生、兄弟以要之。”
為了使官員清廉,清朝獨創了養廉銀制度。當時官員的俸祿很低,七品官年薪45兩銀子,每月合3兩多。按當時一般官吏的生活標準,3兩多銀子只夠五六天的花費。于是地方官在收稅時普遍加收所謂“火耗”,來增加自己的收入。雍正皇帝把這些“火耗”全部收歸國有,然后再從中拿出一部分做養廉銀,把官員的這部分收入合法化。當時縣官的養廉銀在每年1000兩左右。但養廉銀也不能遏止貪污索賄之風。
清朝的官員中,還有不少是捐納得的官———根據當時的制度,士民向國家捐資納粟,就可以取得官職。皇帝通過捐納來增加國家收入。捐納在中國歷史上由來已久,最早出現在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1年)。到西漢時,捐納已經形成制度,但最高只能買到相當于縣令的官職。東漢靈帝賣官明碼標價,張榜公布,現錢交易者還可以優惠。此后歷代都有賣官之舉。到清代,捐納風更盛,康熙時出銀4000兩可捐一知縣,以至全國捐納知縣達500多人。道光時捐一知縣的價碼跌到999兩。按照捐納制度,士民不僅可以捐官,而且可以捐封典、捐虛銜及穿官服的待遇。出錢捐官的人大都是“將本求利”,當上官后很少有不魚肉百姓的,他們中飽私囊,殘民害政,更造成衙門的嚴重腐敗。
捐納知縣手下的師爺,往往都是知縣借貸金店銀號的銀兩時,金店銀號安插的人,是捐官“股份公司”的“股東代表”。這種人惟利是圖,最會貪贓枉法、徇私舞弊,知縣明知也不敢加以阻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