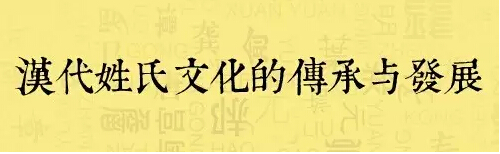精彩推薦
熱點(diǎn)關(guān)注
專題推薦
-
沒有記錄!
熱點(diǎn)排行
漢代姓氏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
2016/8/10 15:24:39 點(diǎn)擊數(shù): 【字體:大 中 小】
劉漢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發(fā)展的第一高峰,是漢民族、漢文化正式形成、并成熟發(fā)展的穩(wěn)固基石,也是中華姓氏承上啟下、發(fā)展定型的歷史時期。
中華姓氏源于上古、延續(xù)至當(dāng)代。在歷史發(fā)展的長河中,中華姓氏發(fā)展演變、延續(xù)傳承,形成了一個內(nèi)涵豐富,體例完備,超越歷史時空,跨越地域界限,包容社會各個層面的文化體系。并以其人人皆有的普及性、世代傳承的連續(xù)性、兼容并包的統(tǒng)一性,博大精深的系統(tǒng)性,縱貫了中華文明的歷史進(jìn)程。從某種意義上講,五千年的華夏文明,就是不同姓氏的宗族群體,在各個歷史時期繁衍生息、播遷交融、興衰更替的總匯。因而中華姓氏成為傳承文明,解讀歷史,剖析社會的獨(dú)特視角和微觀窗口。由中華劉氏創(chuàng)建的大漢王朝,正是中華姓氏發(fā)展史上承上啟下、凝煉升華、成熟定型、并沿用至今的關(guān)鍵時期。
劉漢王朝對中華姓氏形成和發(fā)展的影響,集中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實(shí)現(xiàn)了由“姓氏雙軌”到“姓氏合一”的歷史性轉(zhuǎn)變,形成當(dāng)今中華姓氏的基本模式。
“姓氏雙軌”是指先秦時期姓、氏并存,內(nèi)涵各異,功用不同,界定明確,不得混用的古代姓氏體系;“姓氏合一”則是自西漢以來,姓氏合一,姓氏不分,功用相通,姓氏混用的新型姓氏體系。這是中華姓氏一個重要的發(fā)展演變過程,是古、今姓氏的重大區(qū)別,是中華姓氏體系成熟、定型,并穩(wěn)定發(fā)展的重要標(biāo)志。
先秦時期,“姓”、“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婦人稱姓,男子稱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姓別婚姻,氏明貴賤”。姓是氏的源頭,氏是姓的分支。姓是血緣傳承的譜系,氏是社會地位的標(biāo)志。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西周時的封建宗法制度,由姬姓周天子封邦建國、“胙土命氏”的大小諸侯達(dá)數(shù)十個之多,而這些大小諸侯以國、以邑為氏,形成了姬姓分支的新的氏族。
及至春秋戰(zhàn)國之際,諸侯兼并,長期戰(zhàn)亂,“禮樂崩毀,社會失序”,“姓氏雙軌”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chǔ)日益崩潰。首先是周天子權(quán)威下降,不再具備“胙土命氏”的實(shí)力,諸侯僭越稱位,自立王侯者時有所聞,亡國失氏者屢見不鮮。特別是秦末大起義中,一些社會地位低下的庶民百姓,市井小民,乘勢而起,使植根于封建宗法的“命氏”制度受到毀滅性打擊。如秦末農(nóng)民起義領(lǐng)袖陳勝,就發(fā)出了“帝王將相寧有種乎”的呼聲。一批平民百姓,甚至刑奴屠夫涌入了農(nóng)民起義軍的行列,成為推翻暴秦統(tǒng)治、建立西漢王朝的主力和元勛。如漢高祖劉邦原為泗水亭亭長,漢丞相蕭何為沛縣小吏,梁王彭越原為漁戶,舞陽侯樊噲乃殺狗屠夫,統(tǒng)軍大將淮陰侯韓信則是流浪街頭、乞食于漂母的市井小民,淮南王英布原為被黥刑、刺面的刑奴。這些推翻暴秦、創(chuàng)建漢朝的新貴,均出身寒微,沒有顯貴的家世,自然而然擯棄了原先那種標(biāo)志社會身份地位、以“氏明貴賤”的姓氏制度,對原有的貴族世家進(jìn)行了毫不留情的掃除。據(jù)史書記載,西漢初年,為消滅各地豪強(qiáng)勢力,抑制六國舊族試圖復(fù)國的苗頭,先后將齊、楚、燕、趙、韓、魏六國后裔和豪門大族十多萬人,強(qiáng)行遷徙到關(guān)中諸陵。如齊國公族田氏,因族大人多、遷徙時即按照其居住的宅第,分為八門、八氏,田登為第一氏,田祭為第二氏,田癸為第三氏,田英為第八氏。堂堂一國王族,國破家亡后,不僅淪為庶人、罪民,其姓氏也遭到踐踏,由國姓公族改為毫無意義的序號作為姓氏。
漢代對姓氏制度有重大影響的另一措施,就是實(shí)行“編戶齊民”,對每家每戶進(jìn)行人口登記,標(biāo)明居處、姓氏,便于征納賦稅,進(jìn)行管理。這樣,就使全國百姓,家家戶戶都有了自己的姓氏,是中華姓氏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大措施。
鑒于漢代姓氏制度的重大變革,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首次使用了“姓氏合一”的記述方法。在《史記·本紀(jì)》中,于秦始皇曰:“姓趙氏”,于漢高祖曰:“姓劉氏”。所以清代大學(xué)者顧炎武在其《日知錄》中說:“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而為一。”明確點(diǎn)出了“姓氏合一”始于西漢這一重要的歷史史實(shí)。清代另一學(xué)者錢大昕在《十駕齋養(yǎng)新錄·姓氏篇》中也說:“戰(zhàn)國紛爭,氏族之學(xué)久廢不講。秦滅六雄,廢封建,雖公族亦無議貴之律,匹夫編戶,知有氏而不知有姓久矣。漢高祖起于布衣,……亦不言何姓,以氏為姓”。因而自漢代以后,姓氏合一,“遂為一代之制。”
“姓氏合一”,是中華姓氏史上一個重要轉(zhuǎn)折,是姓氏史上的一大飛躍。其意義在于:
一是姓與氏二者可以通稱共用,姓即氏,氏即姓,姓氏已失去文化內(nèi)涵和功用上的區(qū)別,使先秦時數(shù)量龐大、來源多端的“氏”融入了姓的范疇,極大地豐富了中華姓氏。二是每一個宗族、家庭都有了自己固定的姓氏,子子孫孫世代相承,不必像先秦那樣變來變?nèi)ィ怪腥A姓氏具備了世代傳承的持續(xù)性和人人皆有的普及性。三是取消了姓氏專屬貴族階層的特權(quán),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有姓氏,不再像先秦那樣,貴族有姓有氏,平民有名無氏。使姓氏成為社會個體與生俱來的第一標(biāo)志,日常生活和社會場合通用的信息符號。極大地拓展了姓氏的使用功能和實(shí)用范圍。四是“姓氏合一”有利中華姓氏的延續(xù)傳承,正常發(fā)展,故而留傳至今,永葆青春。中華姓氏至此形成了完整文化體系。劉漢王朝為我們留下的這份珍貴遺產(chǎn),既是漢文化的珍品,也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
二、拓展了中華姓氏的領(lǐng)域,豐富了姓氏文化內(nèi)涵。
縱觀中華姓氏起源、發(fā)展、演變、形成的歷史軌跡,可以看出中華姓氏具有姓源廣博,包羅萬象,持續(xù)傳承,縱貫古今,多元一體,兼容并包,分類科學(xué),自成體系等鮮明特色,是一個系統(tǒng)完整的人文科學(xué)體系。而劉漢王朝正是這一學(xué)科體系的奠基時期。
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自古至今,究竟有多少姓氏,尚無確切統(tǒng)計(jì)。據(jù)明代學(xué)者顧炎武統(tǒng)計(jì),上古三皇五帝時只有22個姓氏,加上五帝以外的其它姓氏大約50個左右,漢代史游所著《姓氏急就篇》僅列130個姓氏。經(jīng)漢魏六朝八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到唐代林寶撰修《元和姓纂》時,收錄姓氏達(dá)到1232個,宋代鄭樵《通志·氏族略》著錄姓氏為2255個。今人杜若甫、袁義達(dá)編著的《中華姓氏大辭典》收錄的古今姓氏達(dá)到11996個,是我們常用漢字的三倍之多。由此可見中華姓氏是一個不斷豐富、發(fā)展的文化體系。
在上述眾多的古今姓氏中,那些來源于兩漢時期,已無法統(tǒng)計(jì),但劉漢王朝確實(shí)在拓展中華姓源的譜系中,作出了重大貢獻(xiàn)。
1、開創(chuàng)了因功賜姓,賞賜國姓的歷史先河。
先秦時期,“因生賜姓、胙土命氏”是姓氏產(chǎn)生的主要渠道,受封的國君、卿大夫往往以所賜封國、食邑立族命氏,形成新的姓氏。但因功賜姓,并賜以皇室國姓,則始于漢代。據(jù)《史記》、《漢書》等史書所載,漢高祖劉邦即位之后,因項(xiàng)伯在鴻門宴上護(hù)駕有功,遂賜以國姓,為劉氏;婁敬也因進(jìn)獻(xiàn)奪取關(guān)中、先定三秦之策,被漢高祖賜以國姓劉氏。此風(fēng)一開,后代歷朝帝王紛紛仿效。如李唐王朝先后就賜予十六位有功大臣、十個歸附的少數(shù)民族、部族為國姓李氏。朱明王朝為褒獎鄭成功的豐功偉績,賜以大明國姓(朱姓),因而鄭成功有“國姓爺”之稱。賞賜國姓,固然是酬勞功臣,籠絡(luò)附屬的政治策略,但相沿成習(xí),成為中華姓氏的一個文化內(nèi)涵。
2、推行了嚴(yán)格的避諱制度,開創(chuàng)了避諱改姓的風(fēng)氣。
避諱改姓發(fā)端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但形成制度則在兩漢時期,如“邦”氏本是孔子弟子邦選的后代,但在西漢初期,因漢高祖名劉邦,“邦氏”被迫改為“國氏”。又因漢惠帝名劉盈,盈氏、贏氏被改作“滿氏”。
東漢初年有高士莊子陵與漢光武帝劉秀為布衣之交,及至劉秀稱帝,傳位于漢明帝時,因明帝名莊,莊氏遂避諱改為嚴(yán)氏(莊、嚴(yán)為近義詞)。此外,如漢文帝名啟,啟氏即改為開氏,漢武帝名徹,徹氏改為通氏,漢宣帝名詢,荀氏改為孫氏,……
避諱改姓,顯示了皇家的尊嚴(yán),此后歷代王朝也紛紛仿效,如敬氏改為恭氏或茍氏、文氏,賀氏改為慶氏……等等,不僅為中華姓氏增加了新的姓源譜系,也為我們學(xué)習(xí)和研究中華姓氏增添了一份情趣。
3、創(chuàng)立了“胡姓漢化”的楷模,奠定了中華姓氏“多元一體化”的格局。
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組成的家庭,中華姓氏是一種“多元一體化”的文化體系。“胡姓漢化”,民族交融,是中華姓氏的一大特色,也是姓氏發(fā)展、壯大的歷史潮流。兩漢王朝正是漢族、漢姓形成的歷史時期,是“胡、漢”稱謂的淵源所自,也是“胡姓漢化”的發(fā)端,因而“胡姓漢化”成為歷代民族交融、姓氏一體化的總稱。顯示了大漢王朝的赫赫威儀,也體現(xiàn)了少數(shù)民族對漢文化的仰慕之情。
兩漢時期,為了平息外患,休養(yǎng)國力,奉行了和親政策,多次下嫁王室公主予匈奴單于,因而不少匈奴后裔依照“從母為姓”的習(xí)俗,改姓劉氏。如劉氏二十五望中的東郡劉氏、雕陰劉氏、河南劉氏,多系匈奴后裔。“五胡亂華”時的劉淵、劉聰,也是匈奴后裔。在漢初四大姓氏“金、張、許、史”中的金氏始祖金日磾,也是匈奴屠休王的后代,入使?jié)h室,留居京城后,因謹(jǐn)慎從事,忠于職守,深得漢武帝喜愛,便依據(jù)匈奴人有祭祀金人的習(xí)俗,賜姓金氏。其子孫后代繁榮昌盛,連續(xù)七世,位居高官,成為西漢初期四大姓氏之首,以致西晉文學(xué)家左思在其著名的《詠史》詩中,發(fā)出了“金張籍舊習(xí),七葉珥漢貂”的感嘆。
由劉漢王朝開創(chuàng)的“胡姓漢化”的先例,不僅是中華姓氏發(fā)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民族交融的典范,對兩漢以來兩千多年的歷朝歷代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如北魏孝文帝實(shí)行改革時,首先從胡姓漢化入手,從鮮卑皇室拓跋氏開始,實(shí)行漢化,改姓元氏,其次王公貴族、文武百官,共計(jì)144個鮮卑姓氏全部改為漢姓。其后李唐王朝、朱明王朝乃至于清末民初都有不少“胡姓漢化”的例證。在當(dāng)今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五十六個少數(shù)民族中,就有四十多個民族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漢族姓氏。“胡姓漢化”已成為傳統(tǒng)文化中“多元一體化”的鮮明特色,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生命力最旺、感召力最大、普及面最廣、凝聚力最強(qiáng)的人文情結(jié),是增強(qiáng)中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橋梁紐帶,是各族人民認(rèn)同中華文明的基石。
三、創(chuàng)立了姓氏研究的多個學(xué)科,奠定了中華姓氏學(xué)的學(xué)科體系。
姓氏學(xué)是專門研究姓氏起源、發(fā)展、類別、演變及其文化內(nèi)涵和社會功能的傳統(tǒng)學(xué)科,也是與歷史學(xué)、社會學(xué)、人類學(xué)、民俗學(xué)、人口學(xué)、倫理學(xué)、譜牒學(xué)多種學(xué)科相互交叉的綜合學(xué)科。由于它是關(guān)乎到血緣傳承、宗法繼嗣的頭等大事,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先秦時期,歷朝歷代,諸侯各國,都有“奠世系、掌譜系”的專職機(jī)構(gòu),世家大族、庶民百姓也十分注重“別婚姻、明繼嗣”的宗法禮儀,因而姓氏文化的積淀非常豐厚。兩漢時期對這一豐厚的歷史遺產(chǎn)進(jìn)行了認(rèn)真總結(jié),形成了一個學(xué)人眾多,著述頗豐的文化現(xiàn)象,開創(chuàng)了姓氏學(xué)中的“族系類”、“地望類”、“考源類”、“考辨類”、“通俗類”及姓氏分類學(xué)多個門類,奠定了中華姓氏學(xué)的學(xué)科體系。
1、開創(chuàng)了姓氏學(xué)中“族系類”的編纂體系。
其中問世最早,影響最大的是《世本》一書。《世本》是中國第一部,也是世界第一部系統(tǒng)性的姓氏譜牒學(xué)著作。關(guān)于《世本》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歷來有兩種說法:一說為戰(zhàn)國時期,史官所作,托名為左丘明所撰。一說成書于西漢初年。唐代劉知幾在《史通·正史篇》中說:“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卿大夫之世系,終于秦末,號曰‘世本’”。因當(dāng)時《世本》原書尚存,劉知幾為著名史學(xué)家,可能得見原書全貌,該書中所記姓氏“終于秦末”,其成書年代當(dāng)在西漢初年。
《世本》一書記述了上起三皇五帝,一直到春秋戰(zhàn)國,迄于秦末的歷代帝王諸侯、卿大夫的姓氏、族系的起源,世系傳承,分支衍派,遷居本末,生前創(chuàng)制,死后名號,以及其它事跡,集各家、各代分散的世系于一書,是我國古代王侯顯貴家族世系、姓氏譜牒的總結(jié)性著作。太史公司馬遷纂修《史記》時,就曾大量地引用了《世本》一書的文獻(xiàn)資料。因此,《世本》一書既是我國先秦史的文獻(xiàn)寶庫,也是漢代以來從事姓氏譜牒學(xué)研究所必備的開山之作,在我國姓氏譜牒學(xué)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奠基作用和示范作用,是姓氏學(xué)中“族系類”的典型代表。
2、開啟了“姓標(biāo)郡望”的歷史先河,創(chuàng)立了“以地望論氏”的學(xué)術(shù)體系。
“郡望”一詞是姓氏文化中的重要內(nèi)涵和專用名詞,是州郡名門望族的習(xí)慣稱謂,它是先秦“胙土命氏”、“氏明貴賤”的傳承演變,也是漢魏以來區(qū)分姓氏等級、門第高低的重要標(biāo)志。我國的郡縣制度發(fā)端于春秋戰(zhàn)國之際,漢承秦制,以州郡作為行政建制。中華姓氏中的州郡地望多冠以秦漢地名,蓋源于此。
先是劉漢皇室為顯示其姓氏血統(tǒng)高貴,自稱為帝堯后裔,定劉氏為“國姓”,高居諸姓之上。繼而又分封宗室子弟于州郡各地,世襲王、侯爵位,據(jù)《漢書》所載,西漢時期先后所封同姓諸王63位,同姓諸侯407位。為區(qū)分庶嫡,識別親疏,早在漢高祖七年(前200年),便“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對龐大的皇室宗支登錄管理。這些王侯、貴胄,世襲蔭封,久居封國,各冠以郡、國地望。如沛郡劉氏、彭城劉氏、梁郡劉氏、長沙劉氏、中山劉氏……形成劉氏“二十五望”。
東漢時,“以地論氏”、“姓標(biāo)郡望”的風(fēng)氣更加盛行。如漢明帝永平年間,樊、郭、陰、馬四大外戚相繼專權(quán),“南陽樊氏”、 “中山郭氏”、“新野陰氏”、“扶風(fēng)馬氏”被稱為“永平四姓”。太尉楊震、司徒袁安等名公巨卿,也以“四世三公”的顯赫門第,被稱為“弘農(nóng)楊氏”、“汝南袁氏”……漢獻(xiàn)帝元康元年(220年,即魏王曹丕代漢的同年),頒布的“九品中正制”,更是以國家政令的形式,將門第閥閱、姓氏郡望作為選用官吏、婚姻嫁娶的首要條件,形成了對后世影響深遠(yuǎn)的門閥士族制度。世家大族的子孫后裔即使遷居它鄉(xiāng)異地或朝代更迭,也仍以其原籍所在或發(fā)祥地的“郡望”作為標(biāo)志,自詡門第,相互標(biāo)榜。
隋唐以后,雖然廢除了州郡建置,實(shí)行開科取士,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權(quán),但以州郡地望區(qū)分姓氏等級和門第高下的風(fēng)氣仍根深蒂固,以“地望論氏”的姓氏學(xué)著述也應(yīng)運(yùn)而生,形成一大學(xué)術(shù)體系。如晉代賈氏的《百家譜》、《魏書·官氏志》、南梁劉孝標(biāo)的《世說新語》、唐代的《氏族志》、《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乃至于宋、明兩代的《百家姓》讀本,多以姓氏郡望進(jìn)行編排,成為中華姓氏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和傳承體系,也是當(dāng)今海內(nèi)外炎黃子孫尋根問祖,聯(lián)宗續(xù)譜的重要依據(jù)。
3、出現(xiàn)了一批考辨姓氏源流及姓氏分類的學(xué)術(shù)專著。
東漢以后,隨著門閥制度的形成,一批世家大族應(yīng)運(yùn)而生,操縱了當(dāng)時的社會政局。為適應(yīng)這一社會需求,由班固等編撰的《白虎通義》、王符撰寫的《潛夫論·志氏姓》、應(yīng)劭編撰的《風(fēng)俗通·姓氏篇》等姓氏學(xué)專著應(yīng)運(yùn)而生,記述了門閥世族的血緣譜系,考辨其源流支派,收錄了當(dāng)時流行的數(shù)百個姓氏,并依據(jù)其得姓受氏的來源,將其分為九大類型:
氏于號、氏于爵、氏于居、氏于謚、氏于官、氏于國、氏于事、氏于序、氏于職。宋代鄭樵的《通志·氏族略》即在此基礎(chǔ)上又細(xì)劃為三十二個門類。
這是我國首次對姓氏進(jìn)行的科學(xué)分類,標(biāo)志著中國的姓氏研究已進(jìn)入了專業(yè)的學(xué)術(shù)階段,也標(biāo)志著中華姓氏文化體系在兩漢時期已初步形成“族系類”、“考源類”、“地望類”、“考辨類”、“通俗類”及姓氏分類學(xué)等學(xué)科,奠定了中華姓氏學(xué)的學(xué)科體系。
4、首次運(yùn)用統(tǒng)計(jì)學(xué)原理載錄當(dāng)朝姓氏,開創(chuàng)了“通俗類”姓氏學(xué)的先例。
為適應(yīng)社會各界對姓氏文化的需求,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又編寫了姓氏《急就篇》。全書共三十二章,以“三言詩”的形式將漢代的130個姓氏予以編排:“宋延年、鄭子方、衛(wèi)益壽、史步昌……”,堪稱中國第一部姓名“三字經(jīng)”,對宋代《百家姓》有很大影響,是姓氏學(xué)中“通俗類”的開山之作。
以上所述,僅是中華姓氏在兩漢時期發(fā)展、演變、成熟、定型的幾個側(cè)面,但也足以看出,兩漢時期在中華姓氏發(fā)展史上的重大作用和深遠(yuǎn)影響,也體現(xiàn)了姓氏文化從漢文化中吸取營養(yǎng)、成熟發(fā)展的依存關(guān)系。漢文化培育了姓氏文化,姓氏文化豐富了兩漢文化,劉漢王朝既是漢民族、漢文化正式形成,并成熟發(fā)展的歷史時期,也是中華姓氏文化發(fā)展、定型的重要階段。
責(zé)任編輯:M005文章來源:南陽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
下一條:沒有了上一條:中國古代的姓、氏、名、字、號
相關(guān)信息
- ·你知道哪52個姓氏是全部起源于河南的嗎?
- ·三教九流與姓氏
- ·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會百家姓拜祖團(tuán)參加丙申年
- ·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會2016年年會在河南省人民
- ·姓氏來源分類談
- ·那些默默消失的姓氏:曾有人姓"馬屎" 未能長久
- ·泉州姓氏調(diào)查:貓、嚇、狼等328個姓氏一人獨(dú)享
- ·評論:一場“姓氏”官司傳遞的倫理文化
- ·評論:姓氏讀音被標(biāo)錯,值得打場官司嗎?
- ·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會受邀參加泰國“第七屆東
- ·專家:希望破譯禹碑“天書”解開大禹治水謎團(tuán)
- ·河南姓氏文化專家稱:中華姓氏皆有規(guī)律可尋
- ·中國的"瀕危"姓氏:"難""死"被評最稀有姓氏
- ·張姓族人發(fā)信抗議山西衛(wèi)視《你貴姓》歪曲姓氏
- ·客家姓氏與人口
- ·最難起名姓氏排行榜:“死”比“操”更難取名
- ·西安少見姓氏盤點(diǎn):銀、邊、羊、亓、么、尼
- ·中國各大姓氏的神秘圖騰
- ·“還”也是姓氏?主要分布在江蘇鹽城、連云港
- ·姓氏分布與人口遷移
- ·古稀老人出版《千家姓》 收集1800多個姓氏
- ·我的姓氏誰做主?——透視姓名權(quán)立法解釋
- ·姓氏也是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
- ·姓氏文化:民族傳統(tǒng)的靜美溪流
- ·臨汾剪紙協(xié)會會長創(chuàng)作百余姓氏圖騰剪紙
- ·郝姓是典型的北方姓氏 元朝末年曾大規(guī)模南遷
- ·錢氏修"百家姓"將錢姓排第2位 錢王妃子姓氏靠
- ·姓氏最早不是一回事:姓別婚姻 氏別貴賤
著名人物
沒有記錄!
精彩展示
沒有記錄!
評論區(qū)
友情鏈接
商都網(wǎng)
中國網(wǎng)河南頻道
印象河南網(wǎng)
新華網(wǎng)河南頻道
河南豫劇網(wǎng)
河南省書畫網(wǎng)
中國越調(diào)網(wǎng)
中國古曲網(wǎng)
博雅特產(chǎn)網(wǎng)
福客網(wǎng)
中國戲劇網(wǎng)
中國土特產(chǎn)網(wǎng)
河南自駕旅游網(wǎng)
中華姓氏網(wǎng)
中國旅游網(wǎng)
中國傳統(tǒng)文化藝術(shù)網(wǎng)
族譜錄
文化遺產(chǎn)網(wǎng)
梨園網(wǎng)
河洛大鼓網(wǎng)
剪紙皮影網(wǎng)
中國國家藝術(shù)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