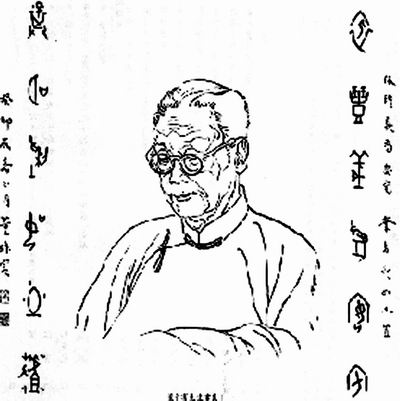-
沒有記錄!
已故甲骨文研究大家董作賓的兒子董敏、董興說:我們的根在河南
2013/9/6 16:41:17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本報訊殷墟申遺成功,安陽不會忘了那些曾經為殷墟做出過貢獻的人們。日前,記者在鄭州見到了來安陽參加慶祝活動的董敏、董興,他們的父親是我國“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賓,河南南陽人。他們為記者講述了一些其父與甲骨文的故事。
游子第一次回故鄉
著名學者陳子展教授在評價早期甲骨學家的時候,寫下“堂堂堂堂,郭董羅王”的名句,這一概括已為學界所廣泛接受。“郭董羅王”,即郭沫若(鼎堂)、董作賓(彥堂)、羅振玉(雪堂)和王國維(觀堂),因為他們的名號中都有一個“堂”字,便有了“甲骨四堂”之說。他們四人在早期的甲骨學研究中各自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今年70歲的董敏和69歲的董興參加完安陽申遺成功慶祝活動后,決定回故里南陽看看。安陽是董作賓成名的地方,而南陽則是董作賓成長的地方。一下子接觸到對父親來說人生中最重要的兩個地方,兩位董先生十分興奮。
土坯墻、竹席頂棚、瓦脊房……這個董作賓先生曾經多次給孩子們講述的老院子如今已經是南陽市的文物保護單位了,門前也掛上了“董作賓故居”的牌子。
董敏告訴記者說:“我聽父親說過,父親小時候家境貧寒,曾輟學當學徒,我這次回老家真是感受到了當時生活的艱辛。父親后來能夠出去求學,多虧了當時南陽的另一位文化名人張中孚老先生的資助,是張老先生把父親帶到北京的。”
董作賓一生育有4個女兒6個兒子,10個孩子分散在中國內地、中國臺灣和美國等地,雖在各自領域取得建樹,但都沒有繼承父親的衣缽。董敏現居中國臺灣,是一個攝影家。董興家住美國,研究交通規劃。董敏、董興兄弟雖然籍貫為“河南南陽”,但此前從未回過南陽。董敏說:“能回老家來尋根,我們感到很高興!”
這次回南陽,董敏、董興拍了許多照片,說是要傳給他們的兄弟姐妹看看。
殷墟的第一次科學發掘
董作賓年輕的時候曾在北京大學講義處抄寫石印講義底稿,為馮友蘭、徐旭生、顧頡剛等所器重,特許他選課做旁聽生。
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董作賓被聘為通訊員,受命到安陽進行殷墟調查。經過實地調查,掌握了第一手資料的董作賓回所匯報了在安陽的考察情況,立即得到重視。隨后,董作賓再次來到安陽,中國文物考古史上首次對殷墟的科學發掘拉開了序幕。
董敏告訴記者說:“當時殷墟盜掘情況很嚴重,還有沒有甲骨誰也不敢肯定。我父親進行了實地調查,認為有發掘的余地。之所以派他來主持發掘,可能是因為他是河南人,比較容易開展工作。當時撥了500元經費,我父親專門到上海買了測量、照相器材,就到安陽開始發掘了。”
安陽殷墟從1928年至1937年科學發掘了15次,董作賓參加了前7次和第9次發掘。這些發掘奠定了我國田野考古學的基礎,培養了一大批考古學專家。他1933年發表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公認是一部中國甲骨文史上劃時代的名著,創立了甲骨斷代學。傅斯年先生將董作賓與東漢張平子作比,稱之為“南陽賢士”,說董作賓“能識倉頡之奇文,詠丘聚之瑋書,發冢以求詩禮于孔丘之前,推步而證合朔于姬公之先”。郭沫若也認為“卜辭研究,自羅、王而外,以董氏所獲為多”。
董敏說:“我采訪過石璋如先生,還看過當時的工作日志。殷墟甲骨藏量最大的坑,編號為‘YH127坑’,可以說是工作人員收工時無意中踢出來的。這個坑藏17096片甲骨,占近百年來發現的15萬片甲骨總量的十分之一。因為現場剝離太慢,決定整體搬遷。64個扛工抬了兩天才抬到安陽火車站,運到南京,當時還拍了一段電影。我父親和胡厚宣兩位先生率技工進行了細心剝離、整理、著錄。此次發現不僅數量驚人,而且整理的刻辭卜甲達300版。其中,有一塊產自馬來半島的龜甲長44厘米、寬35厘米,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大一塊卜甲。當時還請人雕刻了一個甲骨保存狀況的漢白玉模型,現在這個模型還保存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