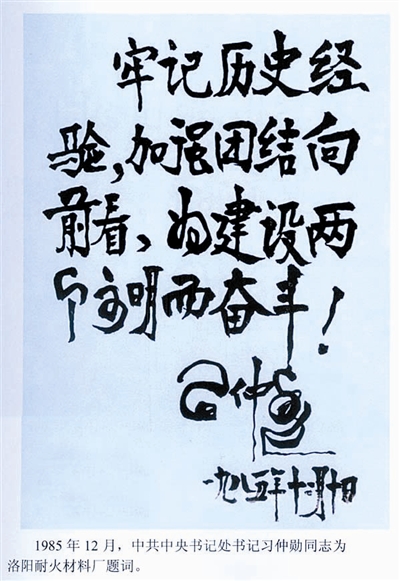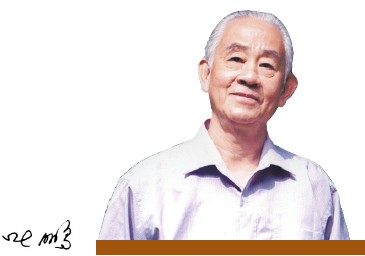-
沒有記錄!
李賀降昌谷 天生詩人質
2012/5/14 10:45:03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一千多年前,宜陽縣昌谷降生了一個奇異詩人,他7歲能詩,揮筆立成;感受事物,敏感多情;渲染物象,色彩紛呈。此人長相怪異,天性驕傲,不屑與同齡兒童為伍,每日滯留于三鄉驛館,與往來東西二京的官員大談詩歌,被人呼為神童——
關于李賀的生平事跡,最早給我們提供資料的,是比李賀稍晚一些的詩人杜牧和李商隱。杜牧為李賀所遺二百多首詩歌作序,李商隱為未曾謀面的李賀寫了小傳。顯而易見,在杜牧和李商隱的心中,李賀是個真正的詩人,他生時嘔心瀝血地作詩,死后被天帝召去寫詩,生生死死,都與詩歌結下了不解之緣。
中唐以來,研究、記述李賀的文人學者何止千萬?即使在我市,研究李賀詩歌和生平的人也很多,但對于一般讀者而言,那些考證文章讀起來了無趣味,倒是近年來出現了一些年輕作者,他們寫活了李賀,講活了李賀,其中宜陽籍學者王愷和宜陽籍作家司衛平,與讀者走得最近,我在敘述李賀生平時,將不時引用他們的新觀點,以便生動解讀詩鬼的形象。
李賀出生之時,東方天空發白
王愷先生的家鄉,離李賀故里只有一公里之遙。在談起李賀的生存環境時,他說,宜陽漢山上的光武廟、子陵殿以及汩汩流動的連昌河、洛河水,還有片片竹園、潺潺溪澗、巍巍山巒,都為詩人成長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這與他后來詩境中的旖旎意象的形成不無關系。
司衛平在《詩鬼李賀》中也描述了李賀的出生地——在距東都120里處的福昌縣(宜陽縣)昌谷,連昌河自西北劈漢山出長巒谷口,匯入洛河。在這兩河交匯形成的一片不大的沖積地上,水木旺盛,鳥語花香,片片瓦屋茅舍掩映在碧綠的竹林當中,深宅院落,尋常巷陌,無不是青竹織墻,翠葉拱頂。有許多的官宦在此安家落戶。
德宗貞元六年(公元790年),一個清風蕩漾的春夜,已是二更時分,家居昌谷長巒谷口的李姓宅院里,依舊燈火通明。堂屋側室的窗欞間,有女子正待分娩。
看了以上描述,我們已經知道——李賀就要誕生了!
查閱史料可知,李賀的母親姓鄭,比李賀的父親李晉肅年齡小了許多,只因原配夫人早死,李晉肅又娶了鄭氏。這次生產,本是頭胎,自然比較費勁兒,捱到雞叫三遍,才有嬰孩呱呱誕生。一聲嬰啼之間,東方正好放亮——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雞一聲天下白”,詩人李賀來到人間。
李家自然是歡天喜地,但孩子出生時,李晉肅卻在陜縣當縣令,不能分享眼下的喜悅,鄭夫人便令一位年輕的長工去報喜。陜縣離此地有二百多里,長工騎上一頭大青驢,匆匆奔上驛道,向西而去。
且說陜縣縣令李晉肅,系唐高祖李淵的叔父鄭王李亮之后。雖出身皇家宗室,但非嫡系,為官入仕數十年,先在西川,后到陜縣,都是七品縣令。如今年過半百,喜得貴子,正如老樹開花,枯藤發芽,不免心花怒放,本應親自回家安慰鄭氏,看望嬌兒,無奈公務繁忙,還須堅守崗位。只好耐住性子,寫了一封書信,由長工帶回。
但他心情過于激動,寫了許多字,感到不達意,寫了揉,揉了扔,如此再三,費去大半天工夫,這邊長工還要急著趕回去復命,都等急了。李晉肅索性只寫了個“賀”字,落了款,叫長工打在包裹內,說:你帶回去吧,夫人自知吾意!
天性帶著文氣,筋脈藏著詩魂
那長工藏了信件,一路趕回宜陽,呈上書信,鄭氏看了,滿紙只有一個“賀”字,認為這是老爺為嬌兒取的名字,返身對兒親了一口說:“兒呀,你父親給你取名李賀哩!”叫著親著,十分歡喜。
今天想來,李賀父親寫的這個字,當是回信的主題,也就是“ 祝賀生子” 的意思,不想李賀的母親望文生義,這小子從此便叫李賀了。后來,老爸又為他取字“長吉”,詩人也便有名有字,只差后人送他一個“詩鬼”稱號了。
李賀滿月這天,李晉肅回來了,當院擺起了酒席,招待親朋好友。老來得子,臉上放光,李晉肅很是高興。不料晚間仔細端詳此兒,越看越覺得怪異——呀!這孩子怎么如此長相?兩條眉毛很長,幾乎連在一起,鼻子大得出奇,臉也長得出奇,手指尖尖,仿若蔥管,再看這小身板兒,如此羸弱,一根細棍似的,似乎天生就有病!
李晉肅確實沒有看走眼,據李賀自己后來寫的詩以及李商隱所撰的《李長吉小傳》中所言,李賀的相貌特征為“細瘦”、“通眉’、“巨鼻”。“通眉”也叫“龐眉”,即兩條眉毛連在一起,而鼻子很是肥大,以至于影響到五官比例。《李長吉小傳》還說李賀“長指爪”,所以后人干脆稱其為“長爪生”。有人說,這種奇特長相,使得李賀寫的詩也很奇特,總是詭秘奇幻,具有詩鬼之潛質。
卻說李賀這棵弱苗,自打出了娘胎,雖然體質孱弱,卻也見風就長,一晃數年過去,小相公別的地方不突出,就是腦瓜子特好使,聰穎絕倫,最愛讀書,常常一個人躲在書房內,翻箱倒篋(qiè),翻撿出一堆書來,席地而坐,讀得津津有味。鄭氏看了,怕他得了孤閉癥,總是攆他出門去玩。
這一日,李賀被母親攆出門來,半天沒回,母親心中高興,說這孩子也該見見太陽,增強一下體質了,可是李賀玩了回來,卻寫了一個字給鄭氏看。鄭氏一看,是個“衢”字,這個字筆畫很稠,小孩子一般不會寫,但李賀偏偏關注最難寫的字——原來,他跑出去啥也不干,專找墳地,去讀墓碑;或到驛館,瀏覽墻壁上的題詩。
文人!天生的文人坯子!天性里帶著文氣,筋脈里藏著詩魂!天降此人,是讓他來寫詩的!母親看著兒子,搖搖頭,不知道說什么好。
留戀三鄉驛館,結識來往官員
這孩子果然很會寫詩。
宜陽這地方,位居東京洛陽和西京長安之間,一條驛路,東西鋪陳,沿著洛河北岸迤邐而去。僅宜陽縣境內,就有五六個驛站,驛站上官員往來,商旅不絕,成了交通的節點和文化的窗口。
司衛平探微:李賀除了讀書練字,還不時四處游走,把附近的驛站都轉熟了。其中三鄉驛館的驛丞姓李,他發現李賀聰明伶俐,又兼同屬李姓本家,所以每每見了李賀,必邀其進館里閑坐,一邊聽李賀背詩誦詞,一邊給李賀講些驛站上的新鮮事。驛丞還把李賀帶到樓上,打開接待高官的客房,讓李賀推窗賞景,看河上船只往來,察天空風云變幻。
一日,吏部侍郎權德輿途經三鄉驛,進驛館小憩。見旁邊坐著一個小人兒在背《詩經》,搖頭晃腦,甚是得意。 就有意挑了幾本不相干的書考他,小人兒竟也背得點滴不差。權侍郎感到很驚奇,又點了《離騷》,李賀見他沒完沒了,便有點不耐煩了,不再聽命,一聲不吭,不背書了。
權侍郎當時穿著官袍,緋衣鮮鮮,儀態威嚴,驛丞畢恭畢敬,不敢怠慢,李賀看了,覺得至于這樣么?并不畏懼,便以沉默來對抗。權侍郎見他頗有個性,教育道:“孺子雖可教矣,但少讀了正經書,將來無成大器了。”誰知李賀竟頂撞起來:“先生差矣!殊不知古人云,痛飲讀《離騷》,非痛飲不可讀《離騷》,而讀離騷正不得不痛飲耳!”
哎呀!三尺玩童,不卑不亢,竟出此言,驚得權侍郎怔在那里,轉而醒悟——這小子是要喝酒呀!于是開懷大笑說:“如此這般,倒是本官小覷了你這垂髫小兒。甚好,甚好!”遂命從人道:“略備些酒菜來,童稚英才,不枉一見,也算是旅途一大趣事。”遂牽了李賀的手,飲酒論詩。
驛丞介紹說:“小公子姓李名賀,是陜縣縣令晉肅公之子。”權侍郎聽了,點了一下頭。李賀嫌驛丞介紹得不夠詳細,便接著說:“我乃大唐宗室鄭王之后,祖籍隴西,祖上是高祖從父李亮的……”自我推介,如數家珍,權侍郎更覺得驚奇。
這李賀飲了酒,把持不住,把玩童的本性恣意地表現了出來。他索來紙筆,說要把自己寫的一首詩寫給權侍郎看,題目是《竹》。他寫道:“入水文光動,抽空綠影春。露華生筍徑,苔色拂霜根。織可承香汗,裁堪釣錦鱗。三梁曾入用,一節奉王孫!”
權侍郎看了,已知此人是奇才,便鄭重地說:“我膝下也有個和你年齡相仿的兒子, 名叫權琚 ,隨其母在東都洛陽家中,將來你們可以交往,相互學習。”臨別,命人取出一方虢州硯,贈給李賀。
驛站成了李賀揚名的平臺,也成了別人認識他的窗口,他小小年紀,詩名是怎樣傳出去的,就是從這里傳出去的,加上三鄉驛驛丞為他做宣傳,兩京往來的官員和商賈都知“昌谷李賀”了。
自古早慧兒童,多是天賦使然
李賀不免驕傲起來,到底是六七歲的小孩兒,經不住別人抬舉,從此出門閑逛,便裝作大人模樣,只到驛站來玩,不屑于與那些同齡兒童為伍。他父親為官多年,未曾有多少浮名,倒是因了這個兒子,每每回來探親,大家都夸他養了一個小神童,不免警覺起來。
這日見兒在家,父親便進行一番說教,不料李賀不服,攔了父親的話頭說:“爹爹的話孩兒記下了,等我長大,要到西京長安考上一科,登龍門如探囊取物一般!”晉肅聽了,嚴厲訓斥起來:“你小小年紀,如此狂狷,難道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師’乎!”
李賀昂首道:“非兒不知道理,實乃那些兒童玩劣!那日我在外游玩,東村王家宅院的公子王參元帶了一群學童與我斗詩,我只一首,便把他們斗敗,他們卻不講規矩,竟把孩兒的詩搶走了!”晉肅問:“確有其事?能否把那首詩背誦給爹爹聽?”李賀便背誦起自己的《新夏歌》來:
曉木千籠真蠟彩,洛蕊枯香數分在。
陰枝拳芽卷縹茸,長風回氣扶蔥蘢。
野家麥畦上新垅,長畛徘徊桑柘重。
刺香滿地菖蒲草,雨梁燕語悲身老。
三月搖楊入河道,天濃地濃柳梳掃。
晉肅聽了,悶聲不語,心中卻喜道:“真乃好詩!此兒天生詩人坯子也!”當下卻不夸他,只是捻著胡須說:“你今后再把《杜少陵集》讀讀!”李賀見爹爹提到杜甫,肅然起敬,不敢再言。只聽夜間爹爹與母親商量“讓他就近先入縣學,學些儒家經典,不至于散漫鄉野”云云。【原標題:李賀降昌谷 天生詩人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