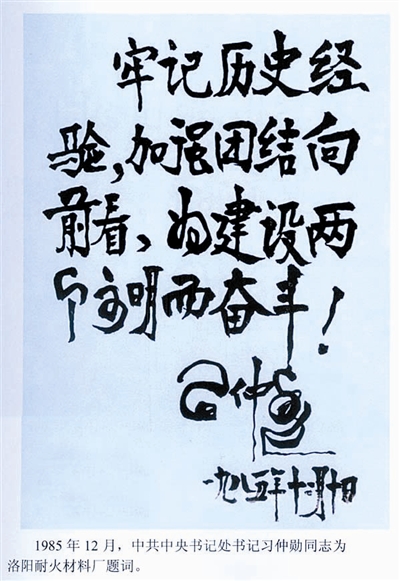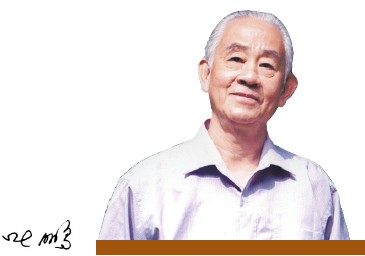精彩推薦
熱點關注
專題推薦
-
沒有記錄!
熱點排行
劉禹錫:失意境遇與詩意連州(下)
2014/12/5 14:21:18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原標題:劉禹錫:失意境遇與詩意連州(下)
寫了《吏隱亭述》,劉禹錫似乎意猶未盡,感覺仍未道盡對連州美景,尤其是對海陽湖的贊美,在《海陽湖別浩初師》詩,他曾寫道:“會吾郡以山水冠世,海陽又以奇甲一州”。于是他又作了《海陽十詠》,全方位,多角度狀寫海陽湖周邊景色。
《雙溪》是其中一首。“雙溪”是指湟川的兩條源流:星子河與淳溪水。其交匯處每到汛期浩浩湯湯,蔚為壯觀,唐代時就是海陽一景。“流水繞雙島,碧溪相并深。浮花擁曲處,遠影落中心。”“雙島”指雙溪匯流以上的兩個小洲:桂林洲與大云洲。這四句詩的大意為:悠悠的流水環繞著兩塊芳草萋萋的綠洲,清清的溪水都能清澈見底。在溪流的彎曲之處擁塞著飄浮的落花,兩岸的青山倒映在河水的中央。后四句“閑鷺久獨立,曝龜驚復沉。蘋風有時起,滿谷簫韶音”連用了三個典故,即“曝龜”、“蘋風”、“韶音”。其出處分別為:“曝龜”一典出自《三秦記》的記載:“河津有一名龍門,兩旁有山,水陸不通,龜魚莫能上。江河大魚,薄集龍門下,上則為龍,不得上,曝鰓水次也。”后來將“曝鰓”比喻為政治上受挫折。唐代詩人錢起《窮秋對雨》中有“始信宣城守,乘流畏曝鰓”之句。“曝龜”即由“曝鰓”中化出。“蘋風”的“蘋”通“萍”,浮漂水上之植物,蘋動即風起,因此楚宋玉在《風賦》中有“夫風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浸淫溪谷,盛怒于土壤之口”之句。“蘋風”即由《風賦》之句中化出。“韶音”,由“簫韶”之典化出。《韶》,舜帝的樂曲名,“簫”見細器之備。韶音即是高雅的帝王之音。了解了詩人所用的這三個典故,再聯想詩人當時所處的背景,我們對這四句詩的理解應當會更深:詩人久久地立在雙溪渡口,想著自己現在的處境就像一只被人遺忘的閑云野鶴。在政治上自己雖然像躍不上龍門的魚龜一樣遭“曝鰓”,但是詩人的雄心壯志還在,只有待到長風再起之時,那時這湟川上下將是一片優雅的王者之音,自己也可一展抱負了。
海陽十景,篇篇涉水,如云英潭“支流日非灑,深處自凝瑩”;飛練瀑“晶晶擲巖端,潔光如可把”;蒙池“瀠渟幽壁下,深凈如無力”;棼絲瀑“飛流透嵌隙,噴灑如絲棼”;裴溪“縈紆非一曲,意態如千里”;雙溪“浮花擁曲處,遠影落中心”;月窟“濺濺漱幽石,注入團圓處”。可見當時的連州既有深潭碧溪,也有飛瀑流泉。詩人還寫了三處亭子:吏隱亭、切云亭、玄覽亭,日軒月影,幽石浮花,香風逼人,清音滿聽,“不以利祿縈心,雖居官而與隱者同”,何其美麗,何其風雅。可以說,從《海陽十詠》這組詩篇中,我們對劉禹錫眼里的連州風景有了更為具象的觀感。難怪開篇《吏隱亭》結句他寫“幾度欲歸去,回眸情更深”,簡直就是現代的表達,簡直可以引來千年后人們的遙遠共鳴,由此足見劉禹錫對連州小城的喜愛和眷戀。
而且,劉禹錫在連州,他的眼里不僅僅有山水之美,更有民生疾苦,對當地民眾包括瑤族瑤民的生活,他都懷了無限的興致,寫下《插田歌》、《采菱行》、《莫謠歌》、《連州臘日觀莫瑤獵西山》、《蠻子歌》等,記述他們的語言服飾,風俗習慣和耕作狩獵場景。比如《插田歌》前六句:“岡頭花草齊,燕子東西飛。田塍望如線,白水光參差。農婦白纻裙,農父綠蓑衣。”用清淡的色彩和簡潔的線條勾勒出插秧時節連州郊外的風光,在工整的構圖上穿插進活潑的動態:岡頭花草嶄齊,燕子穿梭飛舞,田埂筆直如線,清水粼粼閃光。農婦穿著白麻布做的衣裙,農夫披著綠草編的蓑衣,白裙綠衣與綠苗白水的鮮明色彩分外調和。筆墨雖淡,卻渲染出南方水鄉濃郁的春天氣息。
我們知道,劉禹錫的詩歌創作在唐代是獨樹一幟的,他既不像韓愈那樣奇崛怪僻,也不像自居易那么淺俗直露,而是另有一種風味。概括起來,他的詩歌特點是:取境優美,精煉含蓄,韻律自然。這幾個特點,在以上所列舉的《雙溪》、《插田歌》等詩歌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首先是取景,《雙溪》一詩:流水、雙島、碧溪、浮花、遠影、閑鷺;《插田歌》一詩:岡頭、花草、燕子、田塍、水光、農婦、白纻裙,綠蓑衣……寫景抒情、情景交融,構織了一副副優美的圖畫,把讀者帶入如詩如畫的優美境界。而精煉含蓄,韻律自然的特點,讀者早已從其詩行間心領神會,不必多說了。
總而言之,正是透過劉禹錫的詩文,我們得以領略古代連州的山川秀美,同時也感受到這位具有傳奇色彩的詩人在連州活得非常投入,在連州任上作為良多,“功利存乎人民”,各方面都趨于圓熟。劉禹錫失意境遇下仍不失詩意情懷,二十三年的郁郁不得志都頑強拼搏,這種精神在今天來說仍是有深刻的借鑒意義的,而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貢獻,能夠成為一代詩豪,更是當之無愧。(馬忠 清遠市委宣傳部)
寫了《吏隱亭述》,劉禹錫似乎意猶未盡,感覺仍未道盡對連州美景,尤其是對海陽湖的贊美,在《海陽湖別浩初師》詩,他曾寫道:“會吾郡以山水冠世,海陽又以奇甲一州”。于是他又作了《海陽十詠》,全方位,多角度狀寫海陽湖周邊景色。
《雙溪》是其中一首。“雙溪”是指湟川的兩條源流:星子河與淳溪水。其交匯處每到汛期浩浩湯湯,蔚為壯觀,唐代時就是海陽一景。“流水繞雙島,碧溪相并深。浮花擁曲處,遠影落中心。”“雙島”指雙溪匯流以上的兩個小洲:桂林洲與大云洲。這四句詩的大意為:悠悠的流水環繞著兩塊芳草萋萋的綠洲,清清的溪水都能清澈見底。在溪流的彎曲之處擁塞著飄浮的落花,兩岸的青山倒映在河水的中央。后四句“閑鷺久獨立,曝龜驚復沉。蘋風有時起,滿谷簫韶音”連用了三個典故,即“曝龜”、“蘋風”、“韶音”。其出處分別為:“曝龜”一典出自《三秦記》的記載:“河津有一名龍門,兩旁有山,水陸不通,龜魚莫能上。江河大魚,薄集龍門下,上則為龍,不得上,曝鰓水次也。”后來將“曝鰓”比喻為政治上受挫折。唐代詩人錢起《窮秋對雨》中有“始信宣城守,乘流畏曝鰓”之句。“曝龜”即由“曝鰓”中化出。“蘋風”的“蘋”通“萍”,浮漂水上之植物,蘋動即風起,因此楚宋玉在《風賦》中有“夫風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浸淫溪谷,盛怒于土壤之口”之句。“蘋風”即由《風賦》之句中化出。“韶音”,由“簫韶”之典化出。《韶》,舜帝的樂曲名,“簫”見細器之備。韶音即是高雅的帝王之音。了解了詩人所用的這三個典故,再聯想詩人當時所處的背景,我們對這四句詩的理解應當會更深:詩人久久地立在雙溪渡口,想著自己現在的處境就像一只被人遺忘的閑云野鶴。在政治上自己雖然像躍不上龍門的魚龜一樣遭“曝鰓”,但是詩人的雄心壯志還在,只有待到長風再起之時,那時這湟川上下將是一片優雅的王者之音,自己也可一展抱負了。
海陽十景,篇篇涉水,如云英潭“支流日非灑,深處自凝瑩”;飛練瀑“晶晶擲巖端,潔光如可把”;蒙池“瀠渟幽壁下,深凈如無力”;棼絲瀑“飛流透嵌隙,噴灑如絲棼”;裴溪“縈紆非一曲,意態如千里”;雙溪“浮花擁曲處,遠影落中心”;月窟“濺濺漱幽石,注入團圓處”。可見當時的連州既有深潭碧溪,也有飛瀑流泉。詩人還寫了三處亭子:吏隱亭、切云亭、玄覽亭,日軒月影,幽石浮花,香風逼人,清音滿聽,“不以利祿縈心,雖居官而與隱者同”,何其美麗,何其風雅。可以說,從《海陽十詠》這組詩篇中,我們對劉禹錫眼里的連州風景有了更為具象的觀感。難怪開篇《吏隱亭》結句他寫“幾度欲歸去,回眸情更深”,簡直就是現代的表達,簡直可以引來千年后人們的遙遠共鳴,由此足見劉禹錫對連州小城的喜愛和眷戀。
而且,劉禹錫在連州,他的眼里不僅僅有山水之美,更有民生疾苦,對當地民眾包括瑤族瑤民的生活,他都懷了無限的興致,寫下《插田歌》、《采菱行》、《莫謠歌》、《連州臘日觀莫瑤獵西山》、《蠻子歌》等,記述他們的語言服飾,風俗習慣和耕作狩獵場景。比如《插田歌》前六句:“岡頭花草齊,燕子東西飛。田塍望如線,白水光參差。農婦白纻裙,農父綠蓑衣。”用清淡的色彩和簡潔的線條勾勒出插秧時節連州郊外的風光,在工整的構圖上穿插進活潑的動態:岡頭花草嶄齊,燕子穿梭飛舞,田埂筆直如線,清水粼粼閃光。農婦穿著白麻布做的衣裙,農夫披著綠草編的蓑衣,白裙綠衣與綠苗白水的鮮明色彩分外調和。筆墨雖淡,卻渲染出南方水鄉濃郁的春天氣息。
我們知道,劉禹錫的詩歌創作在唐代是獨樹一幟的,他既不像韓愈那樣奇崛怪僻,也不像自居易那么淺俗直露,而是另有一種風味。概括起來,他的詩歌特點是:取境優美,精煉含蓄,韻律自然。這幾個特點,在以上所列舉的《雙溪》、《插田歌》等詩歌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首先是取景,《雙溪》一詩:流水、雙島、碧溪、浮花、遠影、閑鷺;《插田歌》一詩:岡頭、花草、燕子、田塍、水光、農婦、白纻裙,綠蓑衣……寫景抒情、情景交融,構織了一副副優美的圖畫,把讀者帶入如詩如畫的優美境界。而精煉含蓄,韻律自然的特點,讀者早已從其詩行間心領神會,不必多說了。
總而言之,正是透過劉禹錫的詩文,我們得以領略古代連州的山川秀美,同時也感受到這位具有傳奇色彩的詩人在連州活得非常投入,在連州任上作為良多,“功利存乎人民”,各方面都趨于圓熟。劉禹錫失意境遇下仍不失詩意情懷,二十三年的郁郁不得志都頑強拼搏,這種精神在今天來說仍是有深刻的借鑒意義的,而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貢獻,能夠成為一代詩豪,更是當之無愧。(馬忠 清遠市委宣傳部)
責任編輯:C009文章來源:南方日報(2014-04-23)
下一條:沒有了上一條:劉禹錫:失意境遇與詩意連州(上)
相關信息
精彩展示
沒有記錄!
評論區